|
|
|
|
 |
| |
 據考古資料,大約在一百萬年以前的黃河流域中。下游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勞動。生息、繁衍著中國遠古人類。在陝西的藍田。北京的周口店、山西的芮城等地,都發現了古人類的遺址和遺骸。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在這一地區經過十幾萬年的進化和發展,到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間,形成了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即到達原始社會的晚期,在黃河中游及其主要支流洛河、渭河。汾河以及黃河下游北部,均是中華文明薈萃的區域。 據考古資料,大約在一百萬年以前的黃河流域中。下游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勞動。生息、繁衍著中國遠古人類。在陝西的藍田。北京的周口店、山西的芮城等地,都發現了古人類的遺址和遺骸。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在這一地區經過十幾萬年的進化和發展,到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間,形成了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即到達原始社會的晚期,在黃河中游及其主要支流洛河、渭河。汾河以及黃河下游北部,均是中華文明薈萃的區域。
 (一)人參隨人類採集業興起而被發現和利用 (一)人參隨人類採集業興起而被發現和利用
仰韶文化以其分佈之廣大,延續之長久,內涵之豐富,影響之深遠,而成為我國新石器文化中的骨幹,它展現了我國母系氏族制繁榮階段的完整歷史。
除以考古成果全面論證仰韶文化之外,在歷史典籍中記載著遠古時代的傳說,更為具體地說明我國原始農業和醫藥形成的過程。傳說中的神農氏時代,大體上相當於這個時期。在古籍怕虎通.號》中記載;「古之人皆食獸肉,至於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由於禽獸資源不足,獵獲困難,難於滿足原始人類基本生活的需要,則必須採集天然植物充飢。在此過程中,因食用某種植物而愈疾,或因食用某種植物而中毒,便積累了經驗,或吸取了教訓,形成了原始的藥物知識。因為沒有文字,只能口傳身授,世襲相沿。關於神農嘗百草的傳說記述在《淮南子.脩務》之中,謂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這些見於史籍的傳說,與仰韶文化母系氏族制的各項事業發展情況相印證。伴隨著中華民族文明史,人參在仰韶文化中後期作為藥物加以應用,是符合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符合人類認識自然得益於自然的規律的。
 (二)甲骨文、金文早已記載人參 (二)甲骨文、金文早已記載人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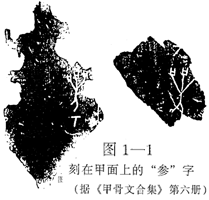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應用人參,並最早用文字記載人參的國家。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應用人參,並最早用文字記載人參的國家。
在我國文字史上,可以辨識的文字以甲骨文為最古老,在商、周時代,把文字刻在龜甲或獸骨之上,是一種相當進步的文字,特稱之為甲骨文。又稱契文。卜辭、殷墟文字。從《甲骨文合集》中查到刻在甲面的「參」字,如圖1一1所示。
圖1—1中編號為17600、17601兩枚甲片的拓片,載於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第六冊2391頁(中華書局1979年12月版),被收於「卜法」之中。
甲骨文始於商殷時代,據今有3500百年以上的歷史。這種文字記載的內容,多為占卜時候刻下的卜辭,偶有記事的文字。上述甲片上的「參」字是象形字,具有人參植株地上、地下部位的典型特徵,且字形粗大古樸,是甲骨文的早期之作。據此可知,我國在3500年之前已經創造出生動形象的「參」字,並有準確可靠的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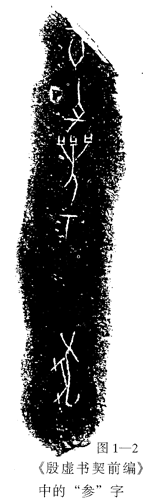 在近代問世的甲骨文代表作《殷虛書契前編》七卷二十五頁第四片(簡稱前七.二五.四)上刻有「參」字(圖1—2)。此字在徐中舒主編的《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古文字字形》兩書中均有收載。現代大型漢字工具書記載的甲骨文上的「參」字,如圖l—3所示。 在近代問世的甲骨文代表作《殷虛書契前編》七卷二十五頁第四片(簡稱前七.二五.四)上刻有「參」字(圖1—2)。此字在徐中舒主編的《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古文字字形》兩書中均有收載。現代大型漢字工具書記載的甲骨文上的「參」字,如圖l—3所示。
我國古老文字中還有「金文」,它是鑄造或雕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又有「鐘鼎文」之稱。商代的金文字體與甲骨文相近;西周的金文字體整齊,辭字漸多,內容多屬祀典、錫命、征伐、契約等;戰國末年,金文字體漸與小篆接近,一般記載督造者、鑄工和器名等。金文中的「參」字在《人參研究》上有專門報道(孫文采,1992),對周早、中、晚金文「參」字有深入的辨析。
在周早的參父乙盉上的「參」字,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象形字,該字為上下結構,中間一橫為地平面,其上為人參地上部分的集中表現,莖上著生多個(古以「三」為多數)核果狀漿果,這是人參最主要的植物學特徵。地平面以下部分是人參的根莖、主根、側根,即入藥部位。自古以來,對人參均認為「如人形者有神」(《名醫別錄》),「人參狀類人形功魁群草」(《醫宗必讀》)。該「參」字下部,如同四肢具備的「人」跪在那裡。這是人參最形象、最有科學意義的真實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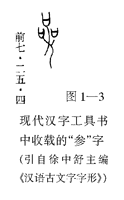
周中舀鼎上的「參」字,其形體與周早父乙盉上的「參」字「母型」相似。該字省去一橫,但地上部分的人參莖和果猶存,特殊之處,是人參之前方多了「三撇」,它代表人參主根上生長有多數側根和鬚根,即古人以「三」為多數,在此又有體現。
周晚彖方彝上的「參」字,與周早父乙盉上的「參」字相似,而周晚克鼎上的「參」字與周中舀鼎上的「參」字相似,都是在保留人參地上部分最大特徵的基礎上,在字形上發生若干變化。及至戰國時代,參字的字形與現代繁體字的「參」相當接近,通用簡化的「參」字,也保留著象形字的特徵。
象形字不是文字圖畫,不可能把事物十分逼真地描繪下來。象形文字只能抓住物體正面、側面或局部,使最主要的特徵變為線條勾勒成文字。它只像自然物典型之形,經過反覆傳習,反覆使用,逐漸定型、表達語意,在金文中「參」這一專用詞有了十分準確的記錄。
至於西漢元帝時代黃門令交遊著《急就篇》中載有「參」字,決不是「參」字之始。因為該篇問世是甲骨文中有「參」字記載的千餘年之後的事情。日本人今村鈵在《人參史》中和日本多種版本的字典、辭典中記載「參」字始載於《急就篇》的觀點是不足取的。尤其《急就篇》是本最為初級的認字讀物,大抵按姓名、衣服、飲食、器具等分類,編成韻語,便於習誦,首句有「急就」(速成之意)二字,故以之命為篇名。就其內容、讀者對像、編寫目的和文體特徵而言,《急就篇》是一本學童用書,在探索字源上沒有權威性。但是,用以證明在西漢時代,對於人參已人人皆知,即使在啟蒙教育中都在傳播「參」的知識,此在人參史上具有更高層次的學術價值。
 (三)人參藥用精髓始載於《神農本草經》 (三)人參藥用精髓始載於《神農本草經》
以仰韶文化中刻在陶器上的符號作為中國文字雛形來計算,中國文字有六干年以上的歷史,然而以文字記事、敘事、立論、著述,當由商代(公元前17世紀至11世紀)和周代(公元前8世紀至前256年)的甲骨文為先導。到秦始皇時代統一文字,直至漢代有各類著作間世。其間,有些流傳至今。《漢書.郊記志》中記載,在公元前31年已有「本草待詔」的稱謂。「本草」泛指中藥,因諸藥中以草為本之意。在《漢書.樓護傳》中敘述,「護少年時候誦讀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可知,當時已有本草專著可供學習之用。由於本草知識日漸豐富,經專門人員整理提高,便產生了我國第一部藥學專著《神農本草經》。

《神農本草經》不是某一位古代本草學專家所著,其內容之豐富,涉及範圍之廣泛,決非一人一時所能完成。之所以加用「神農」之名,正如《淮南子.脩務》所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於神農、黃帝而後入說。」此與前述「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的古代歷史傳說相呼應,可以認為,由原始社會到《神農本草經》成書,全部本草學成就,均由該書所統轄,於其中全面反映出史前時代的藥物學水平,就有關歷史淵源而論,這符合學術上的積累、發展過程,是順理成章的結果。
在《神農本草經》中記載著歷史上形成的人參藥用的精髓,謂「人參,味甘微寒。主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久服,輕身延年。一名人銜,一名鬼蓋。生山谷」。對此藥效精論,現代學者已經用先進的技術和手段進行了考察驗證,確認《神農本草經》中有關人參醫療作用之記載是完全正確的。
《神農本草經》收載藥物365種,其中將藥物分為三類:上品120種,中品120種,下品125種。就其包羅的藥物學知識而言,該書是秦漢以前本草學成就第一次大總結,全面反映了這個時期的藥物學成果。後世稱《神農本草經》是中醫學四大經典著作之一。根據其囊括的本草學內容推斷,這部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藥物專著,成書年代是在秦漢時期(《中醫大辭典醫史文獻分冊》)。即在這個時代,中國對人參的藥用價值已經有了全面總結,形成系統而完整的知識體系,達到古代人參史之最高學術水平。
《神農本草經》原書已佚,有關內容在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唐代蘇敬的《新修本草》、宋代唐慎微的《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都有選載。到達明、清時代,有許多本草學者輯佚,形成了多個版本的《神農本草經》,現有明代盧復輯本,清代黃爽輯本;孫星衍、孫馮翼輯本,顧觀光輯本以及日本人森立之輯本。各種輯本對人參的記載甚為一致,且均列為上品。
現代出版的有尚志鈞《神農本草經校點》,王筠默、王恆芬《神農本草經校正》等。關於人參方面的知識,後者較為豐富。
 (四)漢代是我國重用人參的時期 (四)漢代是我國重用人參的時期
先秦、兩漢時期,是我國醫藥學發展的關鍵時期,其間使古代零散的醫藥經驗上升為系統理論,為後世的醫藥學發展奠定了基礎。漢代,涉及人參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以考古資料為根據編著的《武威漢代醫簡》;在《傷寒雜病論》基礎上,由後人輯成的醫學名著《傷寒論》等。
1972年11月,在甘肅省武威縣旱灘坡漢墓中,發掘出一批漢代醫學簡牘,共92枚。其中簡78枚,牘14枚,如圖1一4所示。考古學者對墓室、棺木結構特點,對殉葬品鳩杖、五銖錢及陶制壺、倉、灶、井、盤等隨葬品,與武威縣磨嘴子大批漢墓出土文物進行比較分析,判定旱灘坡墓的年代為東漢早期所葬。出土的珍貴文物簡牘經過技術處理,除殘破者外,所書文字均可辨認。令人欣喜的是,在1枚簡、2枚牘上,書寫著有人參組成的臨床應用復方。
第77號簡為斷簡殘文,其內容是:
/梵四兩消石二兩人參方風細辛各一兩肥棗五
這枚斷簡的全部內容已無法判定,但從其組方特點可知,這是把人參用於解表、祛風、止痛方面的處方,臨床上用於外感風寒,表證所致諸多疼痛等病症。可以認為人參與辛溫解表藥配伍應用,在漢代已是常用的方法。
第82號犢,為正、背兩面書寫,正面(82甲):
治久洩腸辟□□□□裹□□□□醫不能治皆射去方黃連四分黃芩石脂龍骨人參姜桂各一分凡七物皆並冶合丸以蜜大如彈丸先鋪
背面(82乙):
食以食大飲一丸不知□□□□腸中□二加甘草二分多血加桂二分多農加石脂二分□一□□□□□多□加黃芩一分禁鮮魚豬肉方禁良
上列82乙在圖1一2中省略。
這枚牘記載著治療腸辟(即腸澼)下血、辨證用藥的處方。腸澼的含義有二:(1)痢疾的古稱,(2)便血。本方以清熱燥濕藥為君,收斂止血藥石脂、龍骨為臣,人參、姜桂為佐使,是治療濕熱、痢疾、便血的專方,在強調辨證用藥的同時,隨證加大原方中石脂、桂、黃芩的用藥劑量。
第86號續,為正、背面書寫,正面(86甲):
□□大風方雄黃丹沙□石/茲石玄,石消石/長/一兩人參/之各異/□三重盛藥□□三石□□□三日
背面(86乙):
/熱/上□□十□/飯藥以/豬肉魚辛卅日知六十日愈/皆隨皆復生/雖折能復起不仁皆仁
這是治療大風病的處方。大風又稱癘風、大風惡疾、癲病、大麻風,即現代所稱之麻風病。本方以礦物藥為主,是以祛風攻毒立意而需要療程很長才可收效的方劑。人參在方中協調諸藥,以更好地發揮攻毒作用,並可緩和礦物藥的毒性,以取得更好的療效。
《武威漢代醫簡》中記載的各簡牘,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醫藥著作和珍貴文物,是我國、也是世界上人類記載人參臨床應用情況的最早文獻,在人參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在組方中反映出復方用藥、人參有多方面的應用價值,其歷史意義更應倍加重視。綜合簡牘中對人參應用的情況,可概括出有以下突出特點。
(1)人參被廣泛應用於多種疾病的治療,有一定的用藥規律。
(2)人參的用量相差幅度很大,在劑型和用法上顯示著多樣化。
(3)普遍使用復方,人參在方中的地位因臨床需要而確定。
(4)在人參應用上較《神農本草經》的記載更加具體而準確,應用範圍已經明顯擴大。東漢傑出的醫學家張仲景(張機〕對東漢及其以前的中醫中藥著作去粗取精,結合嚴格的臨床實踐經驗,於東漢末年寫成《傷寒雜病論》一書,該書以六經論傷寒,以臟腑論雜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藥在內的辨證論治原則,總結了東漢以前豐富的醫療經驗,奠定了中國醫藥學辨證論治的理論基礎,對中醫藥學術思想具有深遠的影響。由於東漢時代沒有出版書籍的條件,《傷寒雜病論》在輾轉傳抄中失真分散,至晉代,經王叔和收集整理、編次,形成《傷寒論》一書,這是《傷寒雜病論》中的「傷寒」部分。到宋代,孫奇、林億等進一步發掘古文獻,校訂了《傷寒論》,又把「雜病」部分整理成《金匱要略》一書。直至現代,《傷寒論》、《金匱要略》兩書均為中醫界經典著作,且傳至日本、朝鮮和東南亞等地。
《傷寒論》中載方113首(實為112首,其中禹餘糧丸有方無藥),含有人參者,有21首,占總方數的18.58%。《傷寒論》被譽為「方書之祖」,所收載的方劑,具有不可爭辯的權威性。其中,對含有人參的方劑按現代分類方法加以整理(宋承吉,1984),
可以歸納為以下六類。
1.清熱劑 用於清氣分實熱者有二方:白虎加人參湯方、竹葉石膏湯方。
2.和解劑 屬和解少陽者有五方:小柴胡湯方、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方、桂枝芍葯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方、柴胡加芒硝湯方、柴胡桂枝湯方。屬調和腸胃者有三方:半夏瀉心湯方、黃連湯方、生薑瀉心湯方。
3.理氣劑 共二方:旋覆代赭湯方、厚樸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方。
4.溫裡劑 用於溫中祛寒者有四方:桂枝人參湯方、吳茱萸場方、理中丸方、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方。屬於回陽救逆者有三方:四逆加人參湯方、附子湯方、茯苓四逆湯方。
5.補益劑 僅有一方:炙甘草場方(又名復脈湯方)。
6.驅蟲劑 亦為一方:烏梅丸。
通過以上分類整理,可以瞭解《傷寒論》中含有人參的21個方劑中,其應用範圍具有以下特點。
首先,作為清熱劑、溫裡劑、和解劑應用人參者,共有17方,占含有人參方劑的80%以上。可知,張仲景運用人參,不是現在人們所認為的多做補益藥加以應用,而是以其確切的療效,廣泛用於多種病症。
其次,人參用於「傷寒」、多種熱病,在清氣分實熱、溫中散寒、回陽救逆等多種寒、熱、逆之急症上均用。即發揮人參大補元氣、調營養衛、強心口脫諸項功效,在臨床「應急」上佔有重要地位。
再次,在和解劑中,無論是和解少陽,還是調和胃腸,均屬扶正祛邪、調整機體,發揮多方面藥性溫和的作用。
張仲景大範圍應用人參,擴大其醫療作用,對後世乃至現代,都具有重大影響。《傷寒論》中應用人參的各個方劑,是廣泛應用人參的「醫方先祖」,直至現代,在臨床上仍然具有很強的實用價值。
以東漢醫聖張仲景在《傷寒論》中業已形成的應用人參的規律和體系為根據,應當認定,我國漢代是應用人參的重要時期。
 (五)唐代是我國應用人參的高峰期 (五)唐代是我國應用人參的高峰期
唐代人參的主產區,在「歷史上中國人參資源分佈」中已詳細述及。唐代的人參應用情況,除《新修本草》中有關人參的論述之外,在大量醫學著作中記載得更為全面而具體。而且通過學者和學術上的交流,把中國應用人參的巨大成果傳到了日本。其間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孫思邈及鑒真大師。
孫思邈(581∼682)是唐代著名的醫藥學家,一生拒絕為官,專攻醫事。他學識淵博,精通歷史、醫學和佛學,植根於民眾之中,淡於功名利祿,盡心盡力救危扶困,對唐代醫藥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為歷史留下了寶貴的遺產。他高尚的醫德和光輝的成就,受到後人無限敬仰,尊稱他為「藥王」,在其故里陝西省耀縣立碑建廟。祭祀拜謁,永久紀念。
他所著的《備急千金要方》成書於唐永徽三年(652),其後,孫氏晚年總結近三十年之經驗,補充《備急千金要方》之不足,又撰寫了《千金翼方》一書。兩書除收集唐及唐以前的醫藥論述及方藥之外,尚有大量孫氏本人的臨床經驗和在實踐中積累的體會。此外還采錄了一些印度、高麗的醫學資料。
孫氏在組方遣藥中,非常注重人參的地位與作用。在《備急千金要方》中,沒有本草學的內容,對人參無專論;《千金翼方》中雖對人參有專條記載,但其內容基本上是《神農本草經》和《名醫別錄》二者之融合。令人驚奇的是,孫氏在運用人參組方方面,創造了歷史上的新紀錄,經統計,《備急千金要方》中有445個方含有人參;在《千金翼方》中,有310個方含有人參。
唐王朝全盛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版圖擴大,北界包括貝加爾湖和葉尼塞河上游,西北達裡海,東為日本海,歷史上特稱為「大唐」。其經濟和文化交流,遍及歐亞各地。隨著唐代文化的傳播,中國醫藥科學也逐漸走向世界。日本以派遣學問增和聘請學者前去講學的方式,全面學習和接受中國唐代文化。「唐風」在現代的日本仍有相當多的留存。直到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醫學一直以漢方醫學即中醫學為主流。中醫中藥在日本得以存在和發展,其主要根源植於日本醫藥學始祖——鑒真大師的偉大業績之中。
鑒真大師師徒們應日本大使和學問僧邀請,先後六次東渡,捨生忘死,戰勝重重磨難和險阻,於754年到達日本。鑒真大師把佛學、醫藥學。語言學、哲學、史學、數學.、建築學以及書法知識帶到日本,設佛壇傳佈戒律,與其弟子一道,廣泛傳授各個方面的學問,對當時的日本文化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特別是鑒真大師把中藥辨認鑒定、加工炮製、配伍應用、貯藏保管等知識,親自傳授給日本弟子,使日本有了本草學,因而日本醫學史記載,鑒真是日本本草學的創始人,是日本之「神農」。鑒真當年在日本弘揚佛法。傳授戒律的東大寺,至今還保存和修葺得十分完好,其中有一座日本奈良時代的寶物庫;稱為「正倉院」,該院收藏的寶貴文物中,有大批中藥材。以日本藥學界近代著名學者朝比奈泰彥為首,於20世紀50年代組織全日本學術水平較高的藥學界人士,對每一種中藥材都進行了詳細研究,將研究成果輯成專著,於1955年以《正倉院藥物》為書名正式出版。與人參關係最為密切的是該書系統記載了「正倉院北編號為第122號」的中藥。
用現代科學方法和生藥學研究手段,經過精心研究;保存得比較完好的第122號中藥;大多數是人參根莖(蘆頭〕,少數是人參根部(主根)。在《正倉院藥物》中記載:根莖呈扭曲狀,長10∼15cm,直徑1∼Zcm,外表為黃褐色,有多數地上莖凹痕(蘆碗)連續、密集、交替地分佈在根莖的周圍。在根莖的一凹陷處有麻繩貫穿,這是以繩穿人參進行乾燥時留下的痕跡。地上莖殘痕(蘆碗)有10∼12個,其分佈有不明顯的節段性,有人曾以此為根據,將122號中藥定為「竹節人參」,即把地下莖(人參蘆頭)與竹節人參的根莖混為一談,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令人遺憾的失誤。《正倉院藥物》的作者們,徹底糾正了這一錯誤,將第122號中藥特徵共列出五項,與竹節人參相比較,證明這味中藥是真正的人參,而決不是竹節人參。對人參根,在〈正倉院藥物》中是這樣記載的:根,呈順體,長約5cm,直徑約1.5∼25cm,外表為黃褐色。因遭蟲蛀,顯海綿狀。若是栽培品,可能是生長十五年以上的人參;如是野生者,其生長年限則更久。據此,在《正倉院藥物》中,日本學者們明確肯定:第122號中藥,是產於唐代的人參,如果把它復原,以現代眼光看,它也是最優秀的人參標本(見圖1—5)。這是世界上僅存的歷史最為久遠的人參實物。
我國第一部藥典《新修本草》關於人參主產區的記載,《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兩部巨著中收載大量應用人參的處方,都令人十分信服,唐代在應用人參方面超過了既往的歷史水平。此外,還通過鑒真大師,把我國應用人參的成果傳播到日本。因而,唐代應用人參處於歷史的高峰期。
 (六)宋代是我國應用人參的持續期 (六)宋代是我國應用人參的持續期
五代十國的戰亂,對經濟破壞十分嚴重。宋朝統治者取得政權後即施行改良政策,休養生息,逐漸恢復了農業經濟。在此基礎上,商業、手工業也得到了發展,國內外貿易日趨發達。尤其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官辦校正書局的成立,為出版包括醫藥書籍在內的各種書籍創造了條件。在此期間,一方面,國家系統校訂、刊行了大量醫藥著作,另一方面,醫藥學家個人進行了許多研究和著述,宋代是歷史上整理出版醫藥著作最多。最重要的時期。
宋太宗趙光義(939∼997)在即位之前曾留心醫術,搜集效驗名方千餘首,及至登基後,乃詔翰林、醫官王懷隱、王佑、陳昭遇等人,廣羅單、驗、秘方,吸收了宋以前各種方書的有關內容,編成大型方書《太平聖惠方》,於淳化三年(992)刊行。該書共為100卷,1670門,載方16834首,對方劑、藥物、病症、病理都有論述,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藥完整體系的巨著,對後世有深遠影響,被稱為集方藥之大成的醫籍。由於收方浩繁,對其中有人參的方劑尚未統計,但據推斷其數量不會低於已問世的其他醫藥專著。
宋代個人獨立編著本草書籍很多,其中突出的代表是唐慎微編著的《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簡稱《證類本草》)。唐慎微在醫療活動中,「醫不重酬,但重得方」,收集到民間和歷代本草學大量資料。在此基礎上,又把北宋政府編修的《嘉祐本草》和《本草圖經》融合起來,在元豐五年門(1082)前後編成《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全書32卷,載藥1748種,附圖933幅,已編寫體例嚴謹,對於藥物的別名、藥性、主治、產地。采收、炮製、辨析、附方等,皆有詳細記載。此書規模巨大,內容詳博,藥物眾多,方藥並舉,保存了《神農本草經》以下各主要本草著作的內容,是宋代藥物學的最高成就。在《本草綱目》問世前的五百餘年中,該書一直被視為本草學的範本。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也是以它為藍本編著而成的。李時珍對其保存了大量古代藥學文獻倍加稱頌,認為「使諸家本草及各藥單方,垂之千古,不致淪沒者,皆其功也」。
《證類本草》在人參項下,除對《神農本草經》、《名醫別錄》收載的內容條理分明地加以敘述外,對陶弘景的註釋和《新修本草》的內容也有收錄。唐慎微以「今注」的方式說明:「人參見多用高麗、百濟者。潞州太行山所出,謂之紫團參,亦用焉。」唐氏收錄的關於人參的知識還有掌禹錫等謹案藥性論的內容:「人參惡鹵鹹。生上黨郡。人形者上。次出海東新羅國,又出渤海。主五臟氣不足,五勞七傷,虛損痰弱,吐逆不下食。上霍亂煩悶嘔吵,補五臟六腑,保中守神。又雲馬蘭為之使,消胸中痰,主肺萎吐膿及癇痰,冷氣L逆,傷寒不下食,患人虛而多夢紛壇,加而用之。」據此論述,人參補虛和對呼吸系統。消化系統、神經系統門市。脾、胃、心經)疾病的治療作用,被突出出來,在人參的應用上又向前跨了一大步。《日華於諸家本草》雲人參「殺金石藥毒,調中治氣,消食開胃,食之無忌」。這種見解在說明人參具有解毒作用,可以普及應用,與近世觀點十分相似。
《本草圖經》成書於嘉祐六年(1061),是《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的藍本之一,收載人參的內容可謂十分詳盡。
在距今九百餘年前,對人參原植物的描述及所記載的各個特徵,均真實地說明,該書所收載的上黨人參就是當代的五加科植物真人參(Panax ginseng C A Meyer)。特別值得珍視的是,《證類本草》中所繪的潞州人參(即上黨人參)圖譜,更無可辯駁地證明,我國自古以來使用的人參即為五加科人參的見解是極為正確的(見圖1—6)。在《證類本草》中,還系統而完好地保留了大量本草學文獻,對本草學的考證與研究,對散佚本草書籍的校訂、復輯,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見圖1—7)。
潞州人參圖,以現代植物分類學觀點來看,它也是一幅非常典型的人參圖譜。根,主根、側根、鬚根、根莖(蘆)和不定根(艼)都有較為恰當的描繪,即主根呈圓柱形,有明顯的橫紋;側根從主根分出,漸細,長度長於主根,這是「順體」的特徵之一;鬚根與側根相連,有的自主根伸出,較為稀疏。莖直立,圓柱形。葉輪生於莖頂端,數目依生長年限而不同,葉有長柄,小葉卵形或倒卵形;復葉基部的葉較小,先端漸尖,基部楔形,葉脈顯著。總花便由莖端葉柄中央抽出;頂生傘形花序,有十餘朵或數十朵小花,漿果狀核果隱隱可見。圖譜顯示,我國古代本草學家對人參全株的植物學特點瞭解得一十分深刻。由《本草圖經晰入《證類本草》的這幅人參圖,是世界上最早見於文獻的人參圖譜,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
宋代是我國醫藥著述繁榮的時代,也是應用人參重要的發展時期。特別是宋代的人參主產區明顯向東擴展,增加了人參資源,而且在邊境貿易中通過互市交易,可以獲得相當多的進口人參,保證藥用之需。根據本草著作記載,這個時期應用人參的情況,基本上與唐代相當,口而宋代是繼唐代應用人參達到高峰期之後的持續發展時期。
元朝征服者雖然可使疆域空前擴大,但對經濟和醫藥文化卻只能使之處於停頓狀態。以元朝較有影響的《世醫得效方》為例,其中只有306個方劑應用人參,較歷史水平為低。
 (七)明代是我國應用人參的困難時期 (七)明代是我國應用人參的困難時期
明代自嘉靖到萬曆年間,由於國家統一,政治安定,經濟繁榮,對外交流擴大,陸路和海上貿易發達,有大批藥物湧入我國市場。這一時期醫藥事業興旺,有關論著大批問世。在這些著作中,與人參關係最為密切的是《人參傳》,該書是《本草綱目》的編著者李時珍之父李言聞所著。原書已佚,部分內容被收錄在《本草綱目》中。
《人參傳》在應用人參方面頗有獨到之見,反映出明代對人參從理論到應用都達到很高的水平。《人參傳》記載:「人參生用氣涼,熟用氣溫;味甘補陽,微苦補陰。氣主生物,本乎天;味主成物,本乎地。氣味生成,陰陽之造化也。涼者,高秋清肅之氣,天之陰也,其性降;溫者,陽春生發之氣,天之陽也,其性升。甘者,濕土化成之味,地之陽也,其性浮;微苦者,火土相生之味,地之陰也,其性沉。人參氣味具薄。氣之薄者,生降熟升;味之薄者,生升熟降。如土虛火旺之病,則宜生參,涼薄之氣,以瀉火而補上,是純用其氣也;脾虛肺祛之病,則宜熟參,甘溫之味,以補土而生金,是純用其味也。東垣以相火乘脾,身熱而煩,氣高而喘,頭痛而渴,脈洪而大者,用黃劈佐人參。孫真人治夏月熱傷元氣,人汗大洩,欲成屢厥,用生脈散,以瀉熱火而救金水。君以人參之甘寒,瀉火而補元氣;臣以麥門冬之苦甘寒,清金而滋水源,佐以五味子之酸溫,生腎精而收耗氣,此皆補天元之真氣,非補熱火也。白飛霞云:人參煉育服,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凡病後氣虛及肺虛嗽者,並宜之。若氣虛有火者,合天門冬膏對服之。」
李言聞以中醫藥基礎理論為根據,對人參的應用進行深入而全面的論述;進而用於指導臨床用藥,這在人參史上是僅見的。對以人參為君的生脈散所做方解,以現代醫藥科學水平來衡量,應當認為是權威性的闡述。在《人參傳》中還特別引用孫真人(孫思邈)對生脈散的特殊應用:「夏月服生脈散、腎瀝湯三劑,則百病不生。」即生脈散配腎瀝湯各三服,夏季服用,預防範圍廣泛,治療效果極佳。在現代方劑專著中所載腎瀝湯方有兩個,一個來於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一個來於宋徽宗時由朝廷組織人員編寫的《聖濟總錄》。根據李言聞在《人參傳》中多次引用孫真人的論述,所言腎瀝湯方當來自孫氏名著《備急千金要方》。該書第十九卷載腎瀝湯方的組成。製法和適應症是:
腎瀝湯羊腎一具,桂心一兩,人參、澤瀉、甘草、五味子、防風、川芍、黃芪。地骨皮、當歸各二兩,茯苓、玄參、芍葯、生薑各四兩,磁石五兩。為粗末,先煎羊腎,去腎入諸藥,再煎,分三次服。治勞損,咳逆短氣,四肢煩痛,腰背引痛,耳鳴,面色黑黯,心悸目眩,小便黃赤等症。
本方中人參、五味子與生脈散組成相同,二方合用,實際上是加大了兩味藥的用量。其立意以補益為主,兼有祛風、活血、止痛之功用。所言「百痛不生」,以現代觀點理解,兩方合用可以提高機體免疫功能,增強抗病能力,有預防夏季多種疾病的作用。這是李言聞十分推崇的孫思邈在應用生脈飲中的一個創造,對擴大和重用人參具有積極意義。
李言聞對歷史上名醫名家應用人參的觀點進行了分析整理,頌揚良方,批駁謬誤,發表了深邃的見解。謂「李東垣亦言生脈散、清暑益氣湯,乃三伏瀉火益金之聖藥,而雷學反謂發心炫之患。非也,炫乃臍旁積氣,非心病也。人參能養正破堅積,豈有發炫之理?觀張仲景治腹中寒氣上衝,有頭足,上下痛不可觸近,嘔不能食者,用大建中湯,可知矣。又海藏王好古言,人參補陽洩陰,肺寒宜用,肺熱不宜用。節齋王綸因而和之,謂參。能補肺火,陰虛火動失血諸病,多服必死。二家之說皆偏矣。夫人參能補元陽,生陰血,而瀉陰火,東垣李氏之說也明矣。仲景張氏言亡血血虛者,並加人參;又言肺寒者去人參加乾薑,無令氣壅。丹溪朱氏亦言虛火可補;實火可瀉,芩、連之屬。二家不察三氏之精微,而謂人參補火,謬哉。夫火與元氣不兩立,元氣勝則邪火退。人參既補元氣而又補邪火,是反覆之小人矣,何以與甘草、芩、術謂之四君子耶?雖然,三家之言不可盡廢也。惟其語有滯,故守之者泥而執一,遂視人參如蛇蠍,則不可也。凡人面白、面黃、面青憔悴者,皆脾、肺、腎氣不足,可用也;面赤、面黑者,氣壯神強,不可用也。脈之浮儒虛大遲緩無力,沉而遲澀弱細結代無力者,皆虛而不足,可用也;若弦長緊實滑數有力者,皆火郁內實,不可用也。潔古謂喘嗽勿用者,痰實氣壅之喘也;若腎虛氣短喘促者,必用也。仲景謂肺寒而咳勿用者,寒束熱邪壅郁在肺之咳也;若自汗惡寒而咳者,必用也。東垣謂久病鬱熱在肺勿用者,乃火鬱於內直髮不宜補也;若肺虛火旺氣短自汗者,必用也。丹溪言諸痛不可驟用者,乃邪氣方銳,宜散不宜補也;若裡虛吐利及久病胃弱虛痛喜按者,必用也。節齋謂陰虛火旺勿用者,乃血虛火亢能食,脈弦而數,涼之則傷胃,溫之則傷肺,不受補者也;若自汗氣短肢寒脈虛者,必用也。如此評審,則人參之可用可不用,思過半矣」。
李言聞引述應用人參各家之說,進行了詳細比較、深入分析,闡發了辨證用藥的正確觀點。對恰當應用人參,不畏名醫立論,力求完善,進行了有理有據的論述與評價,這在辨證重用人參的歷史上是一次重大發展,李言聞的功績不可低估。惟李氏在提到醫家姓名時,常名、號並稱或名、姓互稱,給閱讀和理解上帶來一定難度。為較好地體會李言聞的本意,對有關問題略加說明。首先,李言聞贊成李東垣的觀點,批駁了雷敦的錯誤,強調治「炫』的有效方法是用張仲景《傷寒論》中的大建中湯。王好古是元代名醫,號海藏;王綸是明代官吏兼醫家,號節齋。一個說人參補陽洩陰,肺寒宜用,肺熱不宜用;一個競荒謬地稱人參補肺火,陰虛火動失血諸病,多服必死。此二人對人參應用價值的認識是錯誤的。接著,李言聞列舉李東垣(名李果,金代著名醫學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張仲景(名張機,東漢傑出醫學家,後人尊稱為「醫聖」)、朱丹溪(又名朱震亨,元代著名醫學家,「金元四大家」之一)三位權威關於應用人參的見解,進一步批駁了王好古、王綸的謬論。強調對李東垣、張仲景、朱丹溪各家應用人參的成就不能否定,「二王」視人參如蛇蠍的見解是錯誤的。繼之,李言聞非常明確地表明自己關於人參「可用也」、「不可用也」的觀點。之後,解釋了張潔古(名張元素,金代著名醫學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張仲景、李東垣、朱丹溪、王綸等人的諸多見解,同時李氏以肯定的筆觸,強調了「必用」人參的適應症。李言聞認為,經過周詳地審視區分,什麼情況下應用人參,什麼情況下不用人參,需要通過全面思考、細緻辨證後才能確定,不可偏執一說,更不可武斷否定。
李言聞綜合明代以前各個名家應用人參的多種見解,對人參的應用價值做出了定論,這是人參應用史上的一次較全面的總結。而巨,令人真切地體會到李言聞所強調指出的是人參的補益作用及其醫療疾病的重要地位。李氏論及人參在臨床上的應用體現在以下七個方面。
a.用於面白、面黃、面青憔悴,屬脾、肺、腎氣不足者。
b.用於脈浮而沉、虛大、遲緩無力,沉而遲、澀、弱細、結代無力,皆屬虛而不足者。
c.用於腎虛、氣短促者。
d.用於自汗、惡寒而咳者。
e.用於肺虛火旺、氣短自汗者。
f.用於裡虛、吐痢及久病胃弱虛痛喜按者。
g.用於自汗、氣短、肢冷、脈虛者。
此外,李言聞在應用人參之反、畏、惡等用藥禁忌上,也具有獨到的見解。他曾列舉李東垣「理脾胃,瀉陰火,交泰丸內用人參、皂莢,是惡而不惡也」,古方中用四物湯治療婦女閉經症,加用人參、五靈脂,「是畏而不畏也」,還有「療疾在胸隔,以人參。藜蘆同用而取湧越,是激其怒性也」。李氏對這些突破禁忌的臨床用藥方法,倍加讚賞,謂「此皆精微妙奧,非達權衡者不能知」。李言聞稱讚敢於衝破應用人參配伍禁忌的做法,是發揮人參治療作用的創造性發展。這些距今四百多年前的見解,當代臨床醫生和中藥界人士仍難於接受,對人參的反、畏、惡等用藥禁忌視同「雷池」,不敢嘗試著逾越一步。顯然,這方面的研究與探討,有大量工作需要深入進行。
根據李言聞在人參應用方面的全面總結,可知在明代,我國應用人參的理論、臨床辨證用藥的深廣度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自然,這個時期對人參的需求量也隨之增大,使人參在供需之間產生了突出的矛盾。
李時珍編著的《本草綱目》,是我國16世紀以前藥物學知識和用藥經驗的全面總結,是一部在世界上具有廣泛影響的本草學巨著;已有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日文、俄文、西班牙文等多種文字譯本傳佈於世界。李時珍繼承家傳,發揚父願,在《人參傳》的基礎上,對各家本草學的人參精華都做了細緻收集和整理,在《本草綱目》中對人參敘述得最為詳盡,就其內容精深和字數浩繁而言,人參項下所載超出了《本草綱目》中任何一味中藥所能達到的水平。
李時珍在其父《人參傳》的基礎上,總結歷代本草學成果,在人參臨床應用方面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在「附方」項下,李氏整理出67個運用人參的處方,分別應用於15類病症(宋承吉,1989)。
a.用於氣虛欲脫,陰虧陽絕之證,用人參膏。
b.用於脾胃二經各症。用四君子湯、理中湯或與多種藥物配伍組成處方,發揮開胃化痰的功效,治療胃寒氣滿、脾胃虛弱、胃虛噁心、胃寒嘔吐。反胃嘔吐。霍亂嘔惡、霍亂煩悶、霍亂吐瀉、妊娠吐水、心下結氣。
c.用於心經各症。以人參配伍,發揮開心益智功能,主治聞雷即昏、忽喘悶絕。離魂異疾、怔忡自汗、房後睏倦。
d.用於肺經各症:治虛勞發熱、肺熱聲啞、肺虛久咳、止嗽化痰、小兒喘咳、喘咳嗽血、喘嗽吐血、虛勞吐血、吐血下血。
e.用於產前產後:治產後發喘、產後血運、產後不語、產後諸虛、產後秘塞、橫生倒產。
f.用於痢疾:治冷痢厥逆、下痢口、老人痢疾。
g.用於傷寒:治傷寒壞證、傷寒厥逆、夾陰傷寒。
h.用於風證:治筋骨風寒、小兒風癇、脾虛慢驚、驚後瞳斜、痘疹險證。小兒脾風。
i.用於出血證:治出血不止、齒縫出血。
j.用於淋證:治陰虛尿血、砂淋、石淋。
k.用於瘧疾:治虛瘧寒熱。
l.用於消渴證:治消渴引飲。
m.用於酒毒;治酒毒目盲、酒毒生疽。
n.用於咬螫傷:治狗咬風傷、蜈蚣咬傷、蜂王蜇傷。
o.其他,用於肋破腸出,氣奔怪疾。
明代楊起。著有《經驗奇效單方》,他對人參的認識和應用具有代表性,謂「人參功載本草,人所共知。近因病者吝財薄醫;醫復算本惜費,不肯用參療病,以至輕者至重,重者至危」。實際上,是因為人參日缺,參價日昂,醫者、患者皆難於隨心如願地應用人參的結果。楊氏強調人參的藥用地位:「然有肺寒、肺熱、中滿、血虛四證,只宜散寒、清熱、消脹、補營,不用人參,其說近是。殊不知各加人參在內,護持元氣,力助群藥,其功更捷。若日氣無補法,則謬矣。古方治肺寒以溫肺湯,肺熱以清肺湯,中滿以分消湯,血虛以養營湯,皆有人參在焉。所謂邪之所聚,其氣必虛。又曰養正邪自除,陽旺則生陰血,貴在配合得宜爾,庸醫每謂人參不可輕用,誠哉庸也。好生君子,不可輕命薄醫,醫亦不可計利不用。」楊氏申明這些觀點的真意:「書此奉勉,幸勿曰迂。」
李時珍則總結式強調:人參「治男婦一切虛證,發熱自汗,眩暈頭痛,反胃吐食,疾瘧,滑瀉久痢,小便頻數淋瀝,勞倦內傷,中風中暑,萎痺,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治胎前產後諸病」。其用途可謂十分廣泛,顯然,明代及其以前,在人參應用方面的認識,與現代相比,有著懸殊差異。以李時珍整理總結為界,歷史上一直把人參與多種藥物配伍,將其作為具有多種醫療效能的「將士」使用;而今,則多把人參當作僅有滋補作用的「富翁」相待,希冀借助其藥效,達到強身健體、青春常駐。延年益壽之目的。
綜合前述各代人參藥用歷史可知,到了明代,我國應用人參在臨床理論和實踐上已達到歷史的頂峰。然而,人參資源卻受到嚴重破壞,供應遠遠不足。因此,我國在明代,人參的供應和使用已經進入困難時期。
 (八)清代是我國應用人參的衰退時期 (八)清代是我國應用人參的衰退時期
滿族在我國東北興起,建立了清王朝。清代統治者為鞏固其統治地位,在政治、思想。文化上採取野蠻殘酷的高壓政策,大興文字獄,株連滅族,使中華民族優秀的思想火化受到空前的摧殘。在醫藥上,由於知識階層的思想受到禁錮,被迫面向古典醫籍的考據。在本草學方面,限於對既往本草著作的註釋、補充、刪節和改編,興起了所謂「考據學」。反映當時醫藥學成就的本草著述極為稀少,對人參的應用、研究。著述等,也多是因循守舊,遵經衛道,缺乏創新與發展。
前已述及,明代我國人參資源已經遭到全面破壞。至清代,只能使用「遼參」;到乾隆末年,人參的生產與供應已經走向衰退。清朝統治者及其官員們極其腐敗摧毀人參栽培業,到了嘉慶、道光年間,官辦參業已日漸衰落。
高度壟斷,不求發展,摧殘人參栽培業,在野生資源日漸枯竭的情況下,使人參的生產、供應、應用均步入難於挽回的境地。清代有代表性的本草學著作《本草綱目拾遺》(趙學敏撰,刊於1765)中,關於人參應用進展情況毫無記載,而在「參葉」項下則指出「今因遼參日貴,醫輒以之代參,凡症需參而無力用者,輒市葉以代。故今大行為時,蘇州參行參葉且價至三五換不等。以色不黃瘁,綠翠如生,手持之有清香氣者真」。這期間,人參主要供高層統治者和富豪們享用,黎民百姓失去了運用「百草之王」防病治病的能力,於是「參葉」身價大增;堂而皇之代替人參藥用。
在應用人參知識與理論方面,吳儀洛在《本草從新》一書中有較完整的記載。該書對人參的應用價值歸納為:人參甘溫微苦,大補肺中元氣,瀉火,除煩,生津止咳,開心益智,聰耳明目,安精神,定魂魄,上驚悸,通血脈,破堅積,消痰水,治虛勞內傷,虛咳喘促,心腹寒痛,傷寒,嘔吵反胃,淋瀝,脹滿,多夢紛壇,離魂異疾,妊娠吐水,胎產諸虛,小兒慢驚,外科陰毒,因虛失血。氣虛甚者,濃煎獨參湯進之。挾寒者稍加附於。按人參功能在諸藥之上,但氣閉,肺有火熱,及肺氣不利者忌之。表實;表有邪者忌之。凡痘痧斑毒,欲出未出,但悶熱而不見點,若誤用之,以阻截其路,為禍尤烈。產遼東。寧古台(塔)出者,光紅結實;船廠出者,空松鉛塞,並有糙有熟,宜隔紙焙用。忌鐵。不宜見風日。
在人參應用理論方面,黃宮繡在《本草求真》中有較多的闡述,他認為「人參性稟中和,不寒不燥,形狀似人,氣冠群草,能回肺中元氣於垂絕之鄉」。黃氏批駁「第世畏乎其參者,每以參助火助氣,凡遇傷寒發熱,及勞役內傷發熱等症,畏之不啻鴆毒」的極端認識,認為參以補虛,並非填實,主張在元氣素虛,邪匿不出,正宜用參相佐,「用人參內入,領邪外出」。非因外感,而是勞役發熱,亦當用參,關鍵在於「參之所以能益人者,以其力能補虛耳」。強調「虛而氣短,虛而洩瀉,虛而驚恐,虛而倦怠,虛而自汗,虛而眩暈,虛而飽問食滯等,因當用參填補。即使虛而咳血,虛而淋閉,虛而下血失血,與夫虛而喘滿煩躁日渴便結等症」,均可重用人參。用參之道「惟在虛實二字,早於平昔分辨明確,則用自不見誤耳」。黃宮繡的一系列見解,主要集中在人參補虛方面,與現代應用人參的觀點相近。
摘 自:《中國人參》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