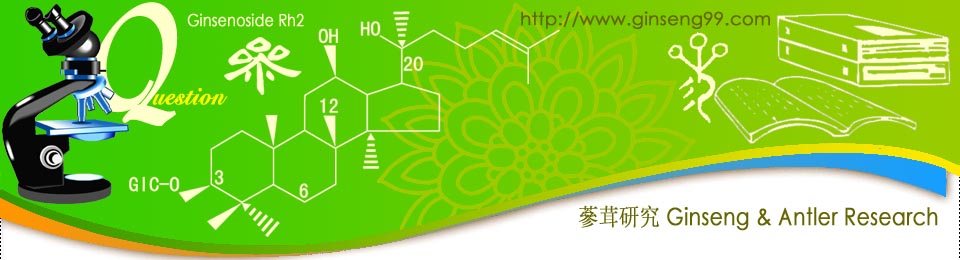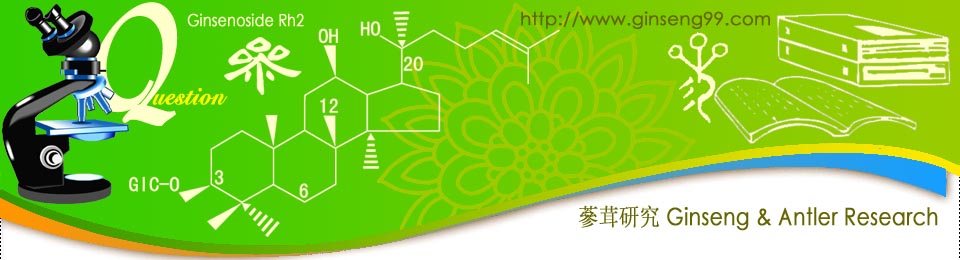|
|
|
|
 |
| |
以嘉慶朝的秧參案為例的探討
蔣 竹 山
 前 言 前 言
清代東北的野生人參是一種對生態環境要求相當高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長的區域有其特定的範圍,其生長的速度也十分緩慢,需要幾年的時間才能長成入藥,由於清初以來官方的大肆開採,從康熙到干嘉時期,東北的參場逐漸有北移的趨勢。隨著人參的開採日漸成為清代內務府的一項重要財源之一,參務管理亦逐漸的官僚化,隆朝時期官參局的設立是重要的表徵。清代東北參務可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剛開始時是「八旗分山制」和「將軍衙門參局制」。明代曾有記載:「奴酋擅貂參之利,富強已非一日。」說明了清入關前的人參採集業已為後金亡明,提供了雄厚的物資基礎。清軍入關,則是東北人參的一次大規模流通。隨著人參在關內的大量輸入,其醫療效用和巨額利潤刺激了關內民眾甘冒巨額風險出關採參。
清入關前實行八旗分山制,規定八旗王公於固定區域採參,彼此不得越境。清初沿襲此制,於寧古塔附近劃定110處參山,規定八旗分山採參。為了要保護人參資源,康熙以來,就對盛京以東、伊通州以南、圖們江以北例行封禁政策。舉凡是移民、田地的墾闢、森林的砍伐、以及人參、貂皮及東珠的掘補,都在禁止之列。清代採參業作為一項特殊的經濟活動持續了近兩百年,經歷了開採、種植、貯藏的過程,取得了寶貴的經驗。但由於清朝的參務政策的失敗,並不能有效地阻止人們的私自挖采,相反地,由於市場需求的大量增長,採參者紛紛栽種秧參,這在嘉慶朝尤其明顯。
乾隆參務案發生後,為了要防制官參局人員因擔任過久的職務而從中舞弊。嘉慶五年起,開始將局員兩年輪調一次。當時的發放官參票的方式是先將本年應放的正票和幫票數額告知各城。收參時由各城副都統派員押送,會同保商、把頭和刨夫帶參包到局。儘管如此,仍難以割除參局直接承辦人的貪污受賄,嘉慶十五年的參務案即是在此背景下發生的。嘉慶參務案的爆發,主要是為了要滿足官參的需要,當時官參局的承辦人員以秧參充當官參,再加上參務管理的不當,參務中出現了上至將軍,下至協領,集體舞弊的情形。嘉慶十三年(1808),北京就已傳出東北的官參摻雜秧參的傳言。到了嘉慶十五年(1810),東北參務各承辦單位都已經在解送的官參中雜摻了秧參。當年二月解交官參時,內務府會同稽查御史共同挑參,東北各地解送官參均有秧參摻入。當時的盛京已有十分之六,而吉林亦達一成,其中盛京四等參六斤內有秧參二斤,吉林四等參三斤二兩及大枝參十兩,竟全是秧參。參局如此欺上瞞下的舉動讓嘉慶皇帝十分震怒,決心查辦吉林參務。此後中央大舉掃蕩秧參及整飭參務,導致參票的發放無法達到官方標準,甚至延伸出更為嚴重的問題。
本文擬透過嘉慶十五年所爆發的秧參案,首先要探討清代東北人參的生態環境變遷與清政府的歇山輪采政策的關連。其次分析秧參出現的原因及其特色。最後論述清政府如何面對秧參的問題,以及秧參案發生後,國家權力的全面介入後對日後參務管理的影響。本文參酌的資料以清代官方檔案為主,例如:《內務府檔案》、《上諭檔》、《清實錄》、《軍機處檔案件》、《宮中檔奏折》、《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嘉慶朝大清會典事例》與《盛京通鑒》。此外,當代學者所編的參務資料集亦是重要參考來源,例如《清代東北參務》和《盛京參務檔案史料》。
 一、人參的生態環境變遷與歇山輪采 一、人參的生態環境變遷與歇山輪采
有關現存史料對清代人參的生態環境的描述,一般並不多見,法國杜赫德神父所編的《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有一段難得類似人類學田野調查式的詳實記載:
「關於這種植物生長的地區,在看到韃靼地圖上標明他們以前,我們大致可以說它位於北緯39度與47度,東京10度與20度(以北京子午線為基準)之間,這裡有綿延不絕的山脈, 山上和四周的密林使人難以進入。人參就長在山坡上和密林中、溪澗旁、峭壁邊、樹下和雜草叢中皆可見蹤影。在平原、河谷、沼澤、溪澗底部及過於空曠的開闊地卻見不到它。如果森林著火並被燒燬,這種植物要在火災後三、四年才能重新生長,若世界上還有某個國家生長此種植物,這個國家恐怕主要是加拿大。」
這是1711年,康熙五十年,住在北京的法國耶穌會教士杜德美神父寫給印度和中國教區總巡閱使的一封信中的一段。換成現在的位置約在中國東北部的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的一部份、烏蘇里江流域、北朝鮮的中部和北部。除了對人參生長環境的描述外,他還推測出有類似生長環境的是加拿大(北美人參)。另外一本較《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早出版的傳教士著作《中國近事報導》也有類似對人參的介紹。
「在中國,有另一類大大不如茶普及的,因而也就更為貴重的藥草,人稱人參。……這是一個約有小拇指一半粗,兩倍長的肥大的根莖。莖分成兩枝,這使得他的外形很像人的兩條腿。顏色近乎黃色:在保存一定時間後起縐並變硬。它的葉子很小,頂端是尖的,枝椏是 黑的,花是紫色的,梗上覆蓋一層茸毛。傳說人參只長一枝梗,這枝梗只分三個杈,每個杈上的葉子四片一簇或五片一簇。人參長在陰蔽的、潮濕的土地上,但生長很慢,要長長的好幾年的時間才能達到完美。人們常在和埃及無花果相差無幾的,叫Kiachu的樹下找到人參。儘管許多地方都出產人參,但質量最佳的人參出Petcij。現在人們使用的是遼東產的,這是位於東韃靼的,附屬於中國的一個省份。」
法國傳教士李明文中的所說的樹名Kiachu可能是五加子科樹,而Petcij可能是泛指中國北疆。有關人參生長環境的記載另外可見於清代的筆記或方志中,清人魏劭卿的《雞林舊聞錄》記有,人參的幼苗的高度有數寸,苗頭平分數莖,每莖五葉,形如掌,六莖為最多,其根株也最佳,有一兩二根莖挖出至美之根者,必定是俗名蘆頭的原根受傷多年,從旁側長出一枝幼苗。《奉天通志》則說,人參春中生苗,多在深山背陰潤濕處,初生小者約三四寸,一椏五葉,四五年後兩椏五葉,未有花莖,至十年後生三椏,年深者生四椏,各五葉,中心一莖,俗名為「百尺杵」。 四月開花,細小如粟,蕊如絲,紫白色,秋後結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等到熟時由青轉為紅,自行掉落。二椏者俗呼為「二甲子」,三椏者為「燈檯子」。挖參者以木製工具挖採人參,禁用鐵器。採得者以松椴的皮和土壤包裡。若是精液枯竭者稱為「啞吧參」,就不值錢。對於人參的生長習性,《全遼備考》亦有類似的說法:「遼東人參,四月發芽五月花,花白,色如韭,叢大者若碗,小若鐘。六月結實,若小豆而連環,色正紅,久之則黃而扁。」
人參、貂皮和烏拉草曾是清代東北相當重要的經濟資源。清人吳樵的《寬城隨筆》有言:
「吉省物產繁伙,寶藏豐富,山水清幽,地力雄厚,既如上所述矣。當地人於土產中尤視為寶貴者,為人參、貂鼠、烏拉草三種。諺云:吉林有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人參在清代除了素有東北三寶的美譽外,另外與吉林的東珠齊名,有「參山珠河」之稱。對於人參的產地和種類,金毓黻的《東北要覽》有以下描述:人參的產地為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北起自興安嶺,南到長白山的山嶽地帶,其總類有三種。(1)山參:產於山間,又稱老山參,數量甚少,價值極貴,每年平均產額約一千五百兩。(2)圓參:為栽培品,當時市面上所販賣的多為這個品種,以寬甸、輯安、臨江、撫松、安圖及汪清等縣栽種最盛,年產約四十萬斤;(3)移山參:大多播種或移植於深山中,經數年後才採集。人參亦為出口品的一種,向以營口為集散地,輸出地大多為內地各省和日本、朝鮮。清人楊賓的《柳邊紀略》則稱:關東人稱呼人參曰「貨」,又名「根子」,肉紅而大者曰「紅根」,半皮半肉者曰「糙重」,空皮曰「泡」,視泡之多寡定貨之成色。
《盛京通志》則載有:盛京東北大山及寧古塔、黑龍江界內生產人參,採參者需領取奉官票採人參,凡是於初夏獲得者曰「芽參」,開花時采收的稱為曰「朵子參」,結霜後採集者叫做「黃草參」,而人參的其它部位如參須、參葉、參子和參膏都是相當珍貴的藥材。至於何時的人參較適合挖采,清人吳桭臣的《寧古塔紀略》記載著「以八九月間者為最佳」。
民國《撫松縣志》曾詳細記載了該地的參業狀況,應可視為是清末秧參業的寫照,所謂:「參有原野之別,人力栽培者謂之園參,天然產於山野者謂之山參,又謂大山參、老山參等名。」該地的人參六月間花落結果,稱為人參果,又稱棒棰,花色紅奪目,採參者於此時採參,稱做「跑紅頭」,大者成柄,即為最佳品,普通者二至五錢或六至八錢就是佳品,二、三兩實是罕見,七、八兩則是百年不遇,只論姿態的優劣,而不份量之輕重。撫松地處邊陲深山,林木密集,常是一 班人結隊成群,入山稱做「挖棒棰」,亦稱「放山」。放山者通常是五至十人持木桿,曰「梭撥落根」。覓參者得參,包於樹皮內,稱為「參包」,在山裡建立一間樹皮房子,朝出暮歸,食宿全在那,自陰曆四月入山,謂之「放芽草市」,五月謂之「放青草市,六月花開謂之「跑紅頭」,七月花落謂之「放韭菜花」(又名:刷帚市)。韭菜花過就到了開秤時期,當白露前二十天,所有放山 者將所得山參包子均帶至集鎮寄放一定處所,公舉一人為經濟掌秤,殆放山者都到期之日,則宰豬、設席、抽煙、賭錢,然後開秤打包,由掌秤者定貨物之優劣及價值之多寡,始可出賣,否則不准買賣,過了白露則扣秤,停止買賣。
由於人參生長環境的限制,所以清代東北主要的參場大多集中在盛京及吉林兩地。康熙年 間,挖參地點只限於烏蘇裡,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又增加了綏芬、額勒敏及哈勒敏三處。乾隆四十七年(1782)戶部議覆盛京將軍永瑋曾因參票開放過多的緣故,奏請歇山:「查,開採參山,原視產參之多寡定下年之開採。額勒敏、哈勒敏參山,自乾隆二十四年奏明開採以後,經該將軍於每歲年底奏請行放參票,已閱二十餘年,自應暫為停歇。」另外一則資料載有盛京將軍清保的奏稱:「查,乾隆十八年烏蘇裡、綏芬等地挖參之事,臣等三處奏准歇山一年。」鳥蘇裡、綏芬二處歸吉林將軍衙門管轄,額勒敏、哈勒敏則是盛京將軍衙門的屬地,但由於參票發放過多,大量採集的結果是地方官員不得不採取歇山的措施。
當清代政府面對有限的參源,民間市場又需求激增的情況時,除了繼續朝較遠的山區開採外,解決的作法就是歇山輪采,換句話說,從康熙到乾隆時期,我們可以發現採參政策有從「擴大參場」到「歇山輪采」的轉變。康熙年二十三年(1684)奏定:「嗣後八旗俱往烏蘇裡等處採參,其分山各入之例,暫時禁止」。清政府取消了八旗分山制,改規定爾後八旗都必須烏蘇裡等處採參,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烏喇(吉林)、寧古塔一帶採取已盡,八旗之地徒有空名」,不得已將參場東移。雖然,康熙朝時,清政府以找尋新的人參產地,來維持人參的產量和需要,解決了部分的人參問題,但這種方法仍然有其局限性,因為人參的自然資源終究有限,在無法管制且大量挖采的情況下,參源不可能維持長久。因此,雍正至乾隆朝才開始以歇山輪采的方式代替擴大參場的政策。據吉林社科院研究員叢佩遠的研究,這種方法始於雍正八年(1730),當時清政府下令烏蘇裡、綏芬等處參山開採兩年,歇山一年,停年之年則改在額爾敏及哈爾敏等地開採。乾隆四十七年(1782)間甚至規定「大小山林輪換歇山」。由於這個政策並不能夠落實,加上私參爛采之風盛行,官方無法全面禁止的情況下,清政府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取消了盛京的歇山制。然而,從乾隆朝開始,在官方的參務管理制度之外,民間卻出現另外一種因應人參生態環境變遷的變通方式——栽種秧參。
 二、參禁制度下的變奏:秧參的崛起 二、參禁制度下的變奏:秧參的崛起
清代東北除了出產野人參外,另外我們可以在醫書、筆記或官方文書中發現秧參——也就是以參苗移植的人參的蹤跡。清人王一元的《遼左見聞錄》就記有當時有人曾經將在千里外深山採集到的人參移至盆栽中作觀賞的用途,他的僕人也曾在采薪時挖到貌似秋葵的人參,這種移盆栽養的人參在秋天時會結紅色果子,但僅有三、四年的壽命。
人參產於邊外深山中,近則千餘里,遠至數千里,開鐵諸邑亦間有。得之者移植盆中以供清玩,余家僮采薪得一本,其葉五椏,略似秋葵,葉每一年則長一節,深秋時結子,殷紅 可愛,閱三四年萎死。
清代有名的植物學家吳其浚(1789-1847)在其名著《植物名實圖考》曾提到:「參本經上品,昔時以遼東、新羅所產皆不及上黨,今以遼東、吉林為貴,新羅次之,其三姓、寧古塔亦試探,不甚多,以苗移植者為秧參,種子者為子參,力皆薄,黨參今系蔓生,頗似沙參苗,根長至尺餘,俗以代人參,殊欠考核。」從這可看出,在清之前,山西上黨的黨參的地位是凌駕於東北的人參和韓國的高麗參之上,到了清代,則移轉到東北人參,產地又以盛京和吉林為主,三姓和寧古塔因數量不多,並未受到重視,此外,有移植的秧參和以參子栽種的子參。
嘉慶年間,刨夫或攬頭為何要用秧參代替人參呢?嘉慶八年,攬頭郝秉純的說法提供了一點蛛絲馬跡。當時領一張參票的刨夫除了官府提供接濟銀兩百兩外,還必須自備兩三百兩銀子,入山以後,有時一天內才找到參苗三、五株,運氣不佳時則好幾天找不到一株,到了深秋時,平均下來,每人僅得參苗二、三錢,最主要的原因是參苗的數量大不如前,因此採參者通常要在春夏青草長長之前比較容易找到參苗,到了秋天草木茂盛時,就難以辨認。由於每領一張參票至少要挖參五、六兩,除了繳交官參外,剩餘人參出售所換得的錢尚須歸還接濟銀二百兩,事實上,刨夫每票所得贏餘相當少,若是碰到不堪蒸做的人參,就必須在地栽養,一直要等到秋天的露水出現後,才起初繳納官參。吉林將軍於嘉慶十五年三月奉聖諭,派親信微服訪查盛京、吉林一帶,發現:「咸稱人參於夏秋之際挖得者津液上貫、根蒂空虛,若當時即行蒸做,不免參質過嫩,交官、出售均難合選。是以每有多帶原土攜回,存儲窩棚暫為培養,伺寒露後始行起做。」這裡提到了夏秋之際挖到的人參的根蒂空虛,若立刻蒸做的話,參質會過嫩,很難賣出好價錢,所以刨夫大多會連土一起挖走,培植在窩棚中。
以養參者王立志為例:王立志來自山東,於嘉慶八年來到吉林,跟著攬頭郝秉純辦參之後, 認領了一張票,夥同十八人入山挖參,在韋山河小營子地方,用樹皮改了兩間秧子房,用土迭成池子,將挖到的參苗,種植在池子裡,有時會買別人所帶來的參苗。池子外面設有一層小棚子,再加一層木柵子,天晴的時候用布棚罩在地上,陰雨時則用席片遮蓋,夜間天氣好時,養參者會將棚子撤走,讓秧參受些露水。王立志並透露出種秧參相當費事,他曾經種了一百多棵參苗,夏天遇到大雨浸爛了,最後只做得一兩多好參,根本都不敷交官。另外,自直隸的劉福昌透露,年六十五歲,在吉林開設酒鋪。嘉慶十二年(1807)才領票辦參,在益通河以東的刷煙河的南誇子屯建有一處秧子房,因為是初次辦參,後來收參時遭夥計摻多了糖水,將人參弄壞。嘉慶十三年時,因栽種的秧子較多,蒸做了八九兩,十四年做得十一兩,除了繳交了官參外,還賣了三百多兩銀子。
根據欽差大臣英和的調查,當時有許多種植秧參的棚廠是由包攬參票的所謂「包門」承領, 以其中一位包門閻錫棟為例,他來自山西的徐溝縣,包攬三十二家燒鍋參票,嘉慶十三年春天,在陽溝邊門的上家子一帶種秧參,後因官府查緝,才移至汪清邊門外(註:吉林靠琿春的北方)的羅圈溝一帶。另外據傅應蘭的供詞,他是奉天承德縣人,包辦五十四家燒鍋參票,嘉慶八年到十年(1803-1805),曾在邊門內尚家河地方設立欄子栽養秧參,十年後移到邊門外李三河營子。山西祁縣的許漢章是另一個例子,包辦三十三家燒鍋參票,嘉慶十三(1808)、十四年(1809)時,曾在汪清邊門內廣法店一帶栽種秧參,後移至羅圈七道溝一帶。36嘉慶十五年,在中央的壓力之下,吉林將軍賽沖阿積極的查辦秧參,從他八月十五日的奏折中,可以看出秧參的種植場所曾散至吉林各處,例如綏芬、英額達的遠山部份,曾燒燬距吉林首府二千里之遠的鷹城子的秧參棚廠,烏雞密西北川干溝子、雞關崖的棚廠,較近的地方有,拆毀東路亮子山的栽參廠棚六處,上江輝法河棚廠七處;西路則有瑪延河(註:吉林通河縣南方)棚廠五處。
秧參的價格會因種植的數量而有所變化。例如嘉慶十五年時,參商潘耕藝和段凌肖就說:「伊等每年十二月到彼,次年三四月回歸,其參系與刨夫交易所種秧參。嘉慶十二年以前頗為得價」。後來因為栽種過多,價格才會下跌,但因為各路皆有出售,所以仍可銷售,不至於不值錢。
商人張晉魁的說法或許能夠反映出當時的商人對於秧參的普遍看法。他認為刨夫之所以栽種秧參,是因為刨夫每張參票能夠帶好幾人入山,他們有的是入山刨參者,有的是隨同看參營者,假若他們在春夏之間就將採集到的人參立刻蒸煮的話,人參的養分尚在枝葉,根部並未茁壯,假使栽種到寒露之後再採取,每棵人參還可以再多個三至五錢不等,但由於大家紛紛改種秧參,秧參的數量過度增加,破壞原有的市場生態,他抱怨當時甚至有人種秧參的時間長達兩三年,雖然顏 色黃嫩許多,但滋味卻相對變薄。
關於籽參的資料,檔案中所記載的較少,遼寧《撫松縣志》所提管到的地方性的園參可代表清末民初的情況。園參的形狀如山參,同由培植者於白露時播種,明年出土,則覆以木板,過 兩年則移植其它園圃,普通移三次即可以做貨,每年做貨在白露節,謂之開鍋,將參由池挖出,僱人洗刷,稱為「刷水子」,俗謂:「婦女刷水子,出貨氣色較好」;又謂人參屬陽,婦女屬陰。 陰陽相生,所以氣色較好。當時原參製作的名稱可分為:(1)「沖參」由園參內挑選姿態佳者,接以露頭、須條精製,與大山等佳者,可充當山參,故曰「沖參」。(2)「洋參」又名大力參,挑選枝頭大者,將須去掉,刮去外皮,然後置於蒸籠蒸熟,取出曝干後為園參上品。(3)「白干」將原參剝去須條,刮去外皮曬乾,即為白干。(4)「生曬」俗名泥漿打滾,將園參由園中挖出,連泥曬乾,不加製造稱為生曬。(5)「紅貨」就是紅參,將參刷洗潔淨,剝去鬍子,加米糠置蒸 籠蒸熟。(6)「唐參」指將參帶須刷淨,置於釜中煮熟,用針扁札多恐,然後將米糖融化,灌飽糖江為度,取出曬乾,裝置木匣,可作為饋贈物品
。
 三、國家權力與秧參:參務案的爆發 三、國家權力與秧參:參務案的爆發
(一)吉林將軍秀林的上奏
吉林將軍秀林於嘉慶七年所提出的開放秧參建議案引發了一連串的秧參調查事件。對我們瞭解嘉慶朝時的國家權力如何全面性的介入參務的管理,有相當大的幫助。以下我們將從幾個主題開始:吉林將軍為何要提出開放秧參的建議呢?這與當時人參的生態環境及參源問題有何關係?最後又引起什麼樣的參務管理的風暴呢?
嘉慶參務案早在嘉慶七年(1802)時就已經顯露端倪,這從日後成為該事件主角的吉林將軍秀林的奏折可見一斑。該奏折的主旨在請旨歇山並准攬頭存留參苗在參園栽種,秀林向中央反應了歷來吉林地區辦理參務所遭遇的實際問題,對秀林而言,這些問題事實上影響到吉林的秧參問題。透過奏折,我們可以瞭解,吉林每年發放參票時,會從資本較充裕的刨夫中,挑選擔任攬頭,率領刨夫入山採參,每票一張配刨夫四名,如果有增加即屬違例。自乾隆三十年(1765)以後,山深路遠,參苗稀出,常無法如數交齊參額,攬頭因此私自增加刨夫挖參,雖然承辦官員皆知道事屬違例,因為攸關上繳官參額數的問題,承辦官員不免會通融辦理。此外,有些沒有參票私自入山的刨夫充斥山區,官府每年拿人參參數百兩之多。要根絕這些,必須請旨、或歇山,然後由寧古塔及三姓副都統帶領官兵前往烏蘇裡、綏芬兩處嚴查。或帶領官兵入冬過冬,次年隨同刨夫旋回,不遺漏任何人,如此散放參票才不至於缺額。
秀林還提到他接任吉林將軍以來,偷挖人參的情形漸漸嚴重,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嘉 慶二年(1797),每次拿獲私參約五、六兩,到了嘉慶三(1798)、四年(1799),拿獲人參已達四十多兩,為了要肅清偷挖人參的情形,他甚至派寧古塔及三姓的副都統帶官兵入山查拿私參。此外,秀林提到商捐的問題,他認為這項銀兩名目是出自參商,但事實上是參商向刨夫購買人參時降低價格,遂以刨夫之有餘補刨夫之不足。秀林所提到商捐起於乾隆三十年(1765)以後,以當時吉林散放參票的慣例,刨夫到參局領票,每張只配四人,但因參苗漸少,攬頭就逐漸加添刨夫,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票眾參缺,承辦官員就在刨夫余參內,每兩收取二十四兩,以作為墊買額參,補抵搨欠的費用,這就是所謂的「商捐」。但到了乾隆五十九年,因搨欠過多,商捐銀兩不敷墊買額參,遂挪移庫項到十四萬兩。此事後來驚動朝廷,乾隆皇帝遂派大學士福康安前往查辦,額票由八百張減為三百張。除了抵補刨夫搨欠的額參,每年還需出銀二萬兩,以抵協領諾穆三、拖蒙阿所虧欠的十一萬兩,最後將商捐改為「參余銀兩」。
上述秀林的奏折透過上溯乾隆朝的參務案,對比出他任內所遭遇的問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求歇山和開放秧參。他最後舉出曾任吉林將軍——現在為大學士的的慶桂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也曾請求歇山為例,要求照例歇山,以使「官兵人等凡遇私挖人犯,一目瞭然,即可立時拿獲,並從嚴治其一罪,使趨利之徒人人咸知警畏,嗣後斷不敢以無票入山,實與散放參票大有裨益矣。」歇山的目的雖然是要查緝私參,但對秀林而言,最嚴重的還是秧參的問題。他在奏折中提到,當時有稱為攬頭的人,領票入山後,若挖到參苗細小而無法蒸做的人參,就會移到參池中栽養,等一兩年後才再挖出,至於剩餘的參苗,每家大概預留二、三十苗,當作隔年的上繳官參。那時四等參是繳交官參的重要項目,為了避免次年的額數不足,秀林想出了權宜之計,他每年派員查驗秧苗棵數,待隔年要驗收四等參時,就指名攬頭繳納那些秧參,所以一旦歇山,也不會影響官參的繳納。
秀林請示歇山及開放秧參的要求並未獲得中央的同意,隨後,戶部駁回了他的要求。戶部認為,以往吉林、烏蘇裡及綏芬等參山停歇開採,原本是為了要培養參苗起見,所以有乾隆二十四年(1759)及四十八年(1783)的歇山。後來因拿獲私參人犯眾多,四十九年(1784)起又照常放票。五十九年(1794)經欽差大學士福康安奏准,減票三百張。嘉慶四年(1799)又經將軍奏准減票五十張,前後合計舊額八百張已經減半,辦理參務理當足夠。之後將軍秀林以私參較多為由,奏請歇山,必定是不能遵照定制嚴格搜查,假使是因為參苗稀少而必須歇山,也應該預先曉諭雲集該城的刨夫,以免各攬頭有所損失。另外,戶部對於秀林將夾帶私人及栽種參苗等有違禁例的事情公然入奏感到不可思議,因此做出決定:「秀林著傳旨申飭。本年照部議,不准歇山,仍遵舊定章程,認真查辦。俟一年後,再將實在情形奏聞請旨。」嘉慶七年(1802)四月二十日,秀林再度上奏,表明燒鍋、參余兩項,暫不能廢止。這是因為吉林參山遼闊,道路叢雜,雖然已經在各主要道路設立卡倫,嚴密查緝,但成效不彰,熟悉山徑的刨夫可能會越過關卡私行挖參,或行於山內吩咐沒有官欠刨夫代為攜出,種種弊端使得有設立參余的必要性。最後,他再次說明開放秧參的功用。乾隆四十二年(1777)以前,吉林並無呈進大枝參和四等參的慣例。四十二年,吉林將軍福康安才開始裝匣恭進。一般刨夫所挖的人參大半過於細小,不符合大枝參和四等參要圓熟的條件,因此刨夫才興起栽養秧參的習慣。從秀林的奏折可看出秧參從乾隆四十三年(1778)起就已出現,明顯地,秀林要求開放秧參的考量,主要是因為要增加上繳官參的數量,而非出於他對吉林一帶的人參產量有逐年減少的觀察,這種非生態環境的考量似乎是凌駕於人參公用的考量。
中央對秀林的訴求的考量又是什麼呢?嘉慶八年(1803)正月二十四,戶部奉上諭駁回了秀林每張參票加添刨夫和開放秧參的訴求。嘉慶八年正月二十四日的上諭有很清楚的論述:嘉慶八年正月二十四日奉旨戶部議駁,吉林將軍秀林奏請參票加夫,並攬頭刨夫仍請准其栽養參苗一折。吉林、烏蘇裡、綏芬等處開採參山,於乾隆年間侍郎金簡等查辦參務章程,早經飭禁收買秧參,上年秀林陳奏歇山培養並奏請將攬頭等存留參苗,仍另在園栽養,亦經部臣議駁,自應遵照辦理,該將軍何得復行瀆請,人參乃地靈鍾產,如果山內獲有大枝人參原應照例呈進,倘實無此項大參,不妨據實聲名,何必用人力栽養,近於作偽乎。況朕向不服用參枝,但揆之物理,山內所產大參,其力自厚,若栽養之參即服用亦不得力,秀林屢請栽種參苗,實屬無謂至每票一張請夫三十二名,與原定四名之數,竟加至七倍,若非吉林承辦參務官員希圖沾潤,藉詞慫恿秀林,縱令多人入山私行刨挖,即系該將軍欲因此漁利,若再不知儆畏,有心藐混,即當特派欽差前往查辦……。戶部以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定制為例,說明以往若每票多添加「余夫」,就必須每名加參五錢,若照秀林所說,明顯是開放讓更多人入山採參,這反而對參苗有害,有前後矛盾之嫌。至於開放秧參是要準備上繳四等匣參,戶部則認為是借口,不必以此偽作的人參充當大枝官參,人參的珍貴靠的就是天然的地靈,秧參無疑是人工的假造品。
(二)中央官員的調查
嘉慶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一封軍機處轉發的上諭打破了盛京、吉林及寧古塔長久以來以秧參混充官參的慣例。這封給山海關副都統領的上諭內容透露出參局與商人串通的不法情事。內務府發現,所收的官參已經連續好幾年摻雜有秧參,以其中最後一次抽查官參的結果為例,寧古塔的秧參有一斤多,盛京秧參有十八斤多,而吉林則有三十七斤之多,而且許多人參中還摻有鉛塊。當時的刨夫領票採參後,除了例行繳交官參外,多餘人參就賣給商人,這些參商進入山海關繳交關稅後,才能將人參販賣至市面上。清朝內閣發現參局常會與商人串通舞弊,以秧參繳交官府,而將品質較佳的人參賣給商販。因此這封上諭特別要求山海關副都統將該處商人所販賣的人參在入關時予以封存,另外由中央派專員解送內務府,並要求參商一同來京城,等到官參與商參一同比驗後才發還給參商。
同日的另一封上諭更清楚地道出,到了嘉慶年間,以往的盛京、吉林和寧古塔一帶環長白山的參場漸漸沒落,採參者必須較以往更往深山中才能採得人參。這些秧參對內閣官員而言,形狀雖黃潤,但性味淡薄,因此大臣所售賣的官參通常價格不高。這封諭旨還談到內務府驗收官參的方式是,稽查御史命各處解員會同經紀鋪戶一起辨識人參真偽有數據顯示,當時盛京的秧參已達六成,吉林的秧參更高達九成。若在驗收過程發現有秧參,各處將軍就必須如數補換,若無法足數,就照兩淮交價之議,分四等、五等及泡丁價格,以銀兩代替人參。這次牽連在內的官員有吉林將軍秀林、盛京將軍富俊、寧古塔副都統富登阿等。依嘉慶十五年三月初六日上諭,原本兵部建議降調革職富俊,但因一時乏人更換,所以從寬留任,至於富登阿則降一級留任,至於該年度上繳的人參,則原參一併發還,以更換好參或自行變價的方式當作賠償。
嘉慶十五年八月,欽差大臣文寧、松寧受嘉慶皇帝之命到吉林調查該地的秧參問題。這兩 位欽差大臣從威遠堡到吉林,一路上沿途密訪,經過伊通河的刷煙一帶,從當地土著口中,得知吉林的山林一帶有許多種參人家所居住的秧子房。在會見吉林將軍賽沖阿後,他們覺得賽沖阿並未據實報告該地嚴禁秧參的成效。
事實上,賽沖阿並未如他所呈報的「業將棚廠燒燬、秧子拔棄。」,在文寧等人的追查之下,驍校騎隆阿才坦承曾經訪查出秧子房的嫌疑犯,但吉林將軍並未下令他確實查辦,所以最後就不了了之。從隆阿提供給欽差大臣的名單中秧子房數目多達十七處,可見秧參在吉林山區的普遍程度。
事實上,嘉慶皇帝早在嘉慶十五年七月就曾得知吉林等地有私種秧參並多收參余銀兩的弊案。當時皇帝曾屢次召見吉林將軍秀林,從秀林的戰慄惶恐的應對中,嘉慶皇帝感覺到必有隱情,所以才派文寧、松寧到吉林來瞭解案情。在七月二十一日,文寧和松寧兩位欽差向皇帝奏報吉林將軍秀林等人涉嫌的參務案:「該處歷任將軍、副都統等無不侵用纍纍………而秀林侵蝕之數為 甚」。這個奏折引起皇帝極大的關切。七月二十七日,文寧收到四百里快騎傳來的上諭,嘉慶皇帝對吉林這次的參務案件做出了重大裁示,下令將秀林革職查抄,其餘涉案官員則分別革審查辦,這次嘉慶參務案的涉案人數之多,牽連之廣,影響之大,不下於乾隆五十九年所發生的參務弊案。秀林因擔任吉林將軍的時間較久,自嘉慶元年至十四年期間侵吞的銀兩,據《清實錄》的記載,高達三萬數千兩之多。此外,轄下官員如薩音保及錢保所分得銀兩亦高達四萬五千八百餘兩;達祿、伊鏗額、布藍泰等人亦侵佔了數千兩。總計約有八萬多兩遭侵吞。為了要查禁秧參,嘉慶皇帝命令新任的地方官立即搜查秧參,私種秧參的攬頭及刨夫亦是追查的重點。八月十四日的上諭甚至要求日後所送的官參不許摻有一枝秧參。
(三)真參的迷思:秧參的查禁
嘉慶十五年的秧參案的查緝重點,如同欽差大臣文寧所說的:「官參之挑選不可不慎、秧參的採集不可不嚴,私參的查拿不可不密,而承辦官員之責成更不可不專。」除了追究失職官員 的責任歸屬外,大致可分為以下四點,(1)官參及商參的重驗、(2)參余銀的調查、(3)刨夫及攬頭 的整頓、(4)查緝私參。
1、官參及商參的重驗
當秧參案發生後,清政府在盛京和吉林的第一要務就是重新檢驗已經上繳的官參。在這之前,以盛京的挑參流程為例,乾隆十年(1745)起,是由京師派員監放監收,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 裁掉京員後,才由盛京將軍會同放票收參。嘉慶五年以來,為避免承辦官員日久從中舞弊,改為兩年調動一次。放票之前,由參局官員就所交船規銀數,本年應放正票、幫票實數告知各城地方官,派員由將軍衙門恩賞銀庫及熊岳、錦州副都統衙門領取應幫銀兩,再就近招募刨夫挖參。到了收參時,由各城地方官押同保商、把頭、刨夫及參包到盛京,然後由盛京將軍督導承辦官員選參。乾隆五十年(1785)以後,參局會從盛京、吉林、寧古塔三處挑選枝大及色澤熟潤的人參,這方法沿用至嘉慶朝。當課參足額,所餘之參就是商參,才准按包封固,核算斤兩來抽稅銀,隨後送入山海關,仍照例繳稅,任商人販賣至民間。參局中的協領在解參過程的角色相當重要。
盛京及吉林將軍是秧參案發生後,負責督導地方參局重新驗參的主要官員。以吉林將軍賽沖阿為例,他剛到任吉林不久,就受命查出所有該年所有呈進及歷年存儲的的四、五等參中的籽參和秧參。據他描述,當時刨夫所栽養的人參是用參苗所種的,而非參籽,其中主要原因是刨夫到山場過遠,採辦困難,採集的山參大多外觀不佳,因而投機轉種外觀較為腴潤的秧參,等秧參成熟後就混雜到官參中,上呈至內務府。後來嘉慶皇帝降旨將各地將軍議處,並將原參發回參商更換好參,或陪繳等值銀兩,假使山中的大參難得,不能如額採辦,可用枝頭較小、重量足數的人參搭配呈進。以盛京為例,以往盛京的挑參官員大多是盛京將軍、侍郎及承辦官員。秧參案發生後,盛京及吉林兩地的選參流程有了變革。最大的變化就是挑參官員層級的提高,由以往盛京將軍和吉林將軍的層級提高到由中央的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或稽查御史出面選參。就中央官員而言,理論上,官參中不該會有秧參,而挑剩的商參更不該會有好參,但從秧參案事後重新驗選官參的結果看來,秧參的比例相當高。嘉慶十五年三月七日的上諭透露,秧參案發生後,擔任盛京侍郎兼管府尹的榮麟表示,每年解參時,曾協助將軍督導承辦官吏共同檢選官參,一般以挑選枝條壯大及顏色紅潤為原則,很難分辨是否為秧參。吉林將軍秀林亦有類似的解釋,他認為在挑選的過程中無法分辨何者是秧參,何者是偽參。
至於在第一線和參商和刨夫接觸的承辦官員,例如協領們,清政府認為他們的經驗豐富,應該比較曉得刨夫設立棚廠栽種秧參的情形,以嘉慶十五年六月十四日的上諭為例,吉林負責參斤解送的協領錢保就必須將吉林所收官參中的秧參及參子播種情形上報中央。當時的地方官員真的能有效地分辨何者是真參、何者是秧參呢?秀林的口供提供了一些線索。據秀林透露,吉林協領錢保曾經教過他如何辨識好參和秧參的差別,所謂:「紅潤的是秧參、帶皮糙的是好參」。但這與秀林的常識相左,所以他在挑參時就選「半截糙皮,半截紅熟的」,最後還表明:「我在京中生長,參之高低,實不能辨認明白。」秀林的反應雖然有可能是推托之辭,但從人參的藥物史的角度來看,清代人參在市面上的種類繁多,人參的物種知識的傳播除了靠經驗傳承外,人參的日用類書的刊刻也加深的人們對人參的認識,但這也反映了要辨識人參的好壞似乎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此許多人參專書──《人參譜》、《參譜》、《人參考》都會在書中教導民眾、醫家或參商如何辨識何者是好參、何者是偽參。
當地方解送到北京的人參發現有秧參時,當時的解決作法是將這些秧參發回原收參地,接下的步驟是叫地方的收參單位再補送官參到中央;其次,若是有缺額,則由地方的父母官分賠。
以嘉慶十五年六月十一日的上諭為例,當內務府駁回官參中混雜的秧參之後,軍機大臣會同總管內務府大臣重新選驗商買余參,這些由吉林、寧古塔解送到京驗選的商買余參,其中又以寧古塔的可用人參較多,至於吉林的秧參的比例就高達十分之八。當時北京商人常會口耳相傳秧參的消息,這提供給中央官員相當好的消息來源。在吉林承辦參務的官員賽沖阿的查明下,由各處駁回的秧參,除了從商參中挑選賠補外,其餘應賠銀數則以兩淮地區的人參販賣價格賠償。由於兩淮地區參價過高,通常四等參要價二百五六十兩兩、五等參要價二百兩,連泡丁都要五六十兩,盛京將軍就曾為此上奏說:「此項參斤雖成數不足,並非民間不用之物」,因而要求每參降至一百餘兩。當地方出現秧參時,失職官員必須攤賠所缺的官參是秧參案後常見之事。榮麟在盛京侍郎兼管府尹任內,因協同盛京將軍富俊挑選山參,所有應繳參價由富俊負責攤陪。此外,一封嘉慶十六年(1811)四月總管內務府的奏折透露,分賠的銀兩是按照職級來分,歷任將軍、副都統分賠四成,官參局局員分賠六成。其中堂官又分為十份,將軍秀林因在位最久應賠六分,歷任各副都統均屬於幫辦,應賠四分。而局員部分亦是以十分核計,協領應賠五分,佐領賠三分,五品以下局員應賠二分。
至於寧古塔挑出的商參,除了抵補內務府的官參外,尚有剩餘人參十二斤三兩,用來留抵吉林遭駁回的官參。此外,中央還派遣英和、初彭齡前往盛京,文寧、松寧兩人前往吉林、寧古塔,並各帶戶部熟悉參務的官員一同前往。這些中央的官員的職責在查明嘉慶十三年吉林、寧古塔報部的參余銀兩為何與在京參商所說的有所出入。該次的秧參調查發現,吉林原解上參98兩4錢、次參2234兩6錢,選得五等參126兩3錢,堪入泡丁92兩1錢,原解泡丁1035兩6錢,選得堪用者49兩、渣末28兩,共合泡丁169兩1錢,參須1692兩3錢。寧古塔原解余參757兩6錢,選得五等參203兩5錢、泡丁59兩。原解泡丁104兩,選得堪用者37兩,連前泡丁共96兩,參須369兩皆不堪用。查前次駁回吉林四等參121兩6錢、五等參648兩1錢、帶鉛泡丁15兩。茲選得吉林余參126兩3錢,泡丁169兩1錢,除應補交泡丁15兩,其餘泡丁154兩1錢,每三兩折五等參1兩,計折五等參51兩3錢6 分,共合五等參177兩6錢6分。吉林下欠四等參121兩6錢,下欠五等參470兩4錢4 分。查前次駁回寧古塔四等參5兩7錢,五等參30兩9錢,帶鉛泡丁5兩。茲選得寧古塔余參203兩5錢,除抵應補交四等參5兩7錢,五等參30兩9錢,尚多餘五等參165兩,選得寧古塔泡丁96兩,除抵應補交泡丁5兩,尚多餘泡丁91兩。
官參中除了摻雜秧參外,有時還回夾帶有插入鉛條的泡丁。例如嘉慶十五年五月十二日的 奏折提到,嘉慶十五年正月,盛京將軍富俊派員解交嘉慶十四年的官參,總管內務府會同稽查御 史查獲秧參一批,立即上奏中央,戶部的指示是:「將挑出之秧參及帶鉛泡丁,著交原解官發回,著落該將軍照數更換,如不能足數,照兩淮變價之例,分別四、五等及泡丁,定價解銀歸款。其如何著落分賠之處,著將軍、副都統等自行酌議辦理」。當時官參中不只常摻雜有秧參及含鉛的泡丁,甚至有以「高麗參之佳者,又何嘗不可充紅潤之正參」或「浸潤礬鹽糖水」來增加重量的情形出現。這些假貨受先會循原運參管道回到各地,由將軍依照原數目更換。此外,假使這些秧參無法完全更新,則必須依照送至兩淮地區販賣的價格,以四等、五等及泡丁的價值換成銀兩,若有不足,則盛京將軍、吉林將軍和寧古塔副都統就必須負責不足銀兩的缺口。那年由內務府解送回盛京的人參總計有:嘉慶十四年的四等參二斤、五等參十八斤十二兩、泡丁一斤四兩, 嘉慶十二年、十三年的四等參十一斤五兩七錢五分、五等參一斤一兩五錢。
除了官參之外,商參是第二波的檢查重點。以嘉慶十五年六月十一日的上諭為例,戶部尚書慶桂將吉林和寧古塔解送而來的商買余參,曾會同參商的經紀人及鋪戶人,在稽查御史富林布、色成額的監督下,共挑選了吉林五等余參126兩3錢、泡丁渣末169兩1錢;選得寧古塔五等余參203兩5錢、泡丁96兩,最後在共同驗收的情況下將這些余參納入正參項目中。挑剩的余參則由參商具領所有該處應賠銀兩,除寧古塔所選余參抵補應交款項,尚有多餘參斤泡丁。其它如吉林下欠參斤,以及盛京駁回的四等參213兩7錢5分、五等參317兩 5錢、帶鉛泡丁20兩,這些駁回的余參則以兩淮地區的人參價格墊賠,五等參每兩三百兩、泡丁每兩一百兩。慶桂發現,除了盛京參商已經將人參運往關內的北京外,吉林所解送的余參大多是秧參,寧古塔則好參較多。透過這則上諭,我們可以看出重新選參是由稽察御史主導,經紀人及鋪戶人則協同在旁。這些解送入京的商參主要是送到內務府,對此,嘉慶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上諭有詳細說明,該年商人所售的人參在入關時就遭到官府截留封固,然後派員解送內務府,並命參商隨同入京,等官參與商參重新審驗後才發還參商販賣。有時,內務府總管太監也負責將庫儲的人參拿出來重新挑參,例如嘉慶十五年二月三十日,內務府總管太監奉旨將十二年、十四年盛京及吉林交到的四等參、五等參取出,連同經紀李廣成、鋪戶劉立觀再行詳加 選驗。
2、參余銀與商幫銀的調查
清廷在商捐之外又設有關稅。在政府官員的眼中,參商賣余參的獲利不小。所以清政府總 是以各種名目向參商徵收銀兩。嘉慶朝秧參的發展迅速,地方政府到了難以控制的局面,參局便轉向販賣秧參的商人徵稅。這種稅收等於公開承認民間興起的秧參買賣的合法性。秧參的發展增加了東北人參的產量,此後,參務管理跟著起了變化。自嘉慶六年(1801)起,因為欽差大臣到吉林查辦公務所需費用,地方上無項可支,官府特立商幫銀項。商幫銀反映了參稅和秧參的內在關係及東北參務難以控制的重大變化,即在參余外另行徵收商賣參稅,盛京則直接在參余中合算稅銀。
參余銀的制度緣起於乾隆年間吉林將軍福康安的構想,其內容是商人購買余參按成色收 銀,作為買補不能進山臥票及墊補刨夫塌欠的用途。秧參案之所以引起中央的注意,絕大因素在於吉林將軍侵吞了參余銀兩三萬兩。《清實錄》對於秀林罪行的記載是:「吉林將軍迄今在任有十五年之久,朕復加恩用為吏部尚書,承受兩朝恩遇,至為優渥,乃因辦理參務,輒私派商幫銀兩,侵蝕至三萬餘兩之多,以至吉林大小官員,人人傚尤,
且該將該處卡倫,私行撤減,至將真參透漏,刨夫等私用秧參,雜摻充數。」嘉慶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秀林侵吞參余銀兩一事,欽差大臣文寧的調查重點在於,首先,究竟官員和參商之間是如何達成參余銀兩額數的共識。其次,由何人經手?這筆款項是由辦參而起,商人所買官參,若獲利不多,何以肯受局員勒索?第三,假若山內官參的獲利不多,參商為何肯出高價購買官參。最後的重點是,每年的真參是如何外流 的?又如何將秧參混雜其中?源起於何年?文寧發現官參之所以外流,與參局官員將官參任由商人私售牟利,以及放任刨夫廣種秧參,雜摻官參有關。對於文寧而言,如何訂立一個較完善的參 務章程,而又不至於讓刨夫裹足不前,拒領參票,是一件相當大的考驗。
此外,戶部尚書慶桂受命調查秧參案,亦發現各處報部參余銀兩是按余參之多寡來定交銀之數目,原則是參多則銀數即減,參少則銀數增加,明顯有參余銀兩與實收數額不符之處。吉林原報部參余銀是4萬6千1百多兩,但從參商潘耕藝的供詞得知,嘉慶十三年時,每余參一兩應交銀十兩,所以總計應是5萬7千7百餘兩,可見吉林將軍少報了1萬1千5 百餘兩。寧古塔原報部的參余銀是1萬8千9百餘兩,經訊問參商段凌霄得知,每余參一兩應交銀十三兩,總計是2萬5百餘兩銀,寧古塔副都統則少報了1630餘兩銀。
3、採參業者的整頓
燒鍋、攬頭及包門是秧參案發生時中央檢討參務管理辦法時的重點之一。大學士慶貴於嘉慶十五年八月十四日曾在議附英和的參務章程時,曾奏稱:「向來參票放與開設燒鍋之人承領,出銀以為幫貼刨夫入山採參之費。」東北的參票管理和燒鍋之間的關係是嘉慶朝的一個特色,它深刻反映出清代東北參務發展的基本狀況,可稱為「燒鍋領票制」。這個制度主要是由燒鍋鋪戶先行出資,交由攬頭代辦,尋覓刨夫採集,或賣參交局。攬頭所僱用的刨夫出參山時,先經參局派專員挑選,剩餘的余參再行交局。這個制度演變至最後,通常是各燒鍋鋪戶領取參票後,並未能有空閒時間去招攬刨夫,反而是將承領參票繳給包門人代為尋覓刨夫。每年包門人平均約有十、七八家至二十餘家不等,每家承領燒鍋參票張數約二、三百張。若招攬到刨夫,他們就會各自帶著刨夫、賬房、器械出邊,設立營子挖參。挖到大枝人參就立即蒸做,枝小者則暫時培養,待秋後再蒸做,統一由蛤螞河章封送進邊界。到了參局,這些包門人就充作各燒鍋字號,代替繳參,事實上,燒鍋鋪戶在整個挖參過程都未參與,所有設立參園栽種秧參皆是因為包門的緣故。這些包門在地方上都是有錢有勢人家,英和的建議是比照吉林的慣例,找尋地方可靠人士充作攬頭,由參局局員作保,革除包門名色,每年參票還是交由燒鍋承領參票。
英和的建議最後獲得大學士慶貴的認同,此後,官設攬頭成為定例,這對官方而言,一方 面可方便稽核;另一方面可能免除包門人從中壟斷。欽差大臣文寧對此現象也有清楚的描寫。根據他的調查,當時吉林的參票發放,大多是交給攬頭,有時一人會領票四、五張,有的是一人領票十餘張,然後任憑攬頭交給刨夫。這使得合格的刨夫幾名、余夫幾名,都無從查對。此外,刨顧慮若將余夫報給官府,就必須按數繳交官參,所以通常會裝作不知;而參局又擔心刨夫若領票會散漫無紀,樂於將參票交給攬頭。攬頭從此易任意把持,任意帶私人入山挖參,導致官參日少,秧參漸多。吉林將軍賽沖阿也曾提到:「該燒鍋行戶承領票張,多系出資交給攬頭代為買參交 局」的現象,主要意思是說燒鍋每領一張參票,就出制錢二百二十千文,交攬頭等代買,而攬頭等承辦此項官參,又是在刨夫出山到參局挑選之後,將剩餘人參購買交局。每當到了限期,參枝無可更換,不能不將就驗收,因此每年解進官參無法避免的質量稱差不齊。
除了燒鍋領票的方式有所改變外,刨夫們在山中過冬種參的情形亦是改革的重點。欽差大臣文寧研擬的十一條參務章程中就有五條是與刨夫及私參有關。以查緝黑人潛匿山內過冬該項為例,就訂有:「預期由吉林將軍將吉林、寧古塔、三姓、伯都納、阿爾楚喀副都統開列名單具奏,恭請簡派二員,酌帶官員兵役,冬季分路進山搜查。凡遇私刨、私種,在山潛匿過冬黑人,飭令官兵嚴拿,照例治罪。系官員拿獲者,酌加獎賞。若收穫私參,向例每參一兩,八錢入官,二錢充賞,折給銀一兩。現當整頓參務,應照例家優,每參一兩賞銀十五兩,准於例收參余項下動支,造冊報部,參入官。」這樣的參務章程的執行成果如何,從吉林將軍賽沖阿向中央回報帶領官 兵搜查烏蘇裡大山的奏折可見一斑。嘉慶十六年十月四日,間隔文寧提出的參務章程一年兩個月的時間,我們可以看到地方官員大規模搜山的動作持續在進行。該年的查緝參山任務是由松寧及 色爾觀執行。松寧自四月二日由吉林帶兵啟程,於十四日抵達寧古塔,十八日由攝河卡倫進山,自磨刀石兵分三路,中路由松寧帶兵至黃泥河一帶搜查;南路的著名參山的綏芬,指派佐領舒倫 保、德克津保及防禦德慶領兵五十人,於柳樹河一帶搜查;另一著名的參山烏蘇裡的北路則交由 佐領圖勒彬、烏爾滾泰領兵五十人於半拉窩棘一帶搜查。其成效分別有:五月十九日,於牛心山 至蘇城查獲有住房培養參苗之刨夫李士紀九名,計參苗五百六十四苗。五月二十三日,於呼葉河 二道溝住房,查有種參苗之刨夫朱洪一名,參苗三百八十八苗,又在途中拿獲出山的走私者王票、 翟永泰,搜獲熟參各兩錢五分。六月一日,於蘇城東南黃溝地方,查有住房培養參苗的刨夫孟君 寶一名,計參苗七十八苗;在窩棚培養參苗的刨夫王殿然、孫吉二名,計參苗三百二十四苗。又 於六月十六日,查有夾皮溝住房種參苗的刨夫一名,計參苗五十五苗。六月十七日,查有住房培養參苗之刨頭劉自名一名,參苗三十九苗,他們的查緝行動一直到八月二十五日才結束。
4、查緝私參
清政府不僅只是在山中查緝秧參的栽種,還加強了私參的查緝。例如欽差大臣文寧的參務 章程中,就擬定要加強搜查潛匿在山中過冬的黑人。對中央而言,大規模的驅逐在山區過冬的走私者,不僅可以減緩真參的流落市面,還可以預防秧參的栽種,當時官方查緝的範圍擴大到吉林、寧古塔、伯都吶、阿爾楚喀等地。卡倫的增設亦是清中央政府的關懷重點,其 目的在防範山場、稽查私參。例如秧參案爆發後,清政府將以往取消的卡倫重新復原,由六、七 座增加至十二座。另外一位欽差大臣英和更詳定了卡倫官兵查獲私參的 記功辦法。每拿獲私參一起,該處將軍記功一次,累積至五次則記名待升。此外,依照舊例,每 參以八錢入官,兩錢當作獎賞。海口沿岸亦是查緝的重點。當時偷挖的私參多由海口前往山東登 州府銷售,官方除了在奉天的旅順及牛莊等海口嚴格查禁外,並令登州水師總兵撥派各兵於與奉天海口相對的登州及萊州加強查緝私參。
這樣的查緝行動不僅在嘉慶十五年展開,還一直持續到嘉慶末年。嘉慶十八年七月,喜明 上奏綏芬和烏蘇裡山一帶連年巡察嚴密,已無刨夫夾帶私人刨參之事,因此請求停派官兵駐冬搜查私參。從內閣回復喜明的奏折可看出,當時查緝私參已從固定定點改為機動的巡察。另外,嘉慶二十二年六月,有鑒於盛京每年秋天派侍郎帶領官兵多人巡察海口已有成效,查無走私人參,盛京將軍富俊遂上奏建議停派侍郎帶員巡查海口,內閣因此下令原本的制度回歸為由當地海口之城的守尉協領及州縣廳員繼續加強查緝私參。
 四、中央與地方的角力:參務章程的論爭 四、中央與地方的角力:參務章程的論爭
秧參案發生後,東北的參務管理除了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處處可見國家權力的介入以外, 另外亦引發朝廷重臣與地方官員對參務章程的論爭。各中央大臣紛紛提出各自對參務的改革意見,共計有吉林將軍賽沖阿、大學士慶桂、欽差大臣英和及文寧等人提出了參務章程的改革。吉林將軍賽沖阿於嘉慶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首先提出「參務章程十二款」,同年七月初二,大學士慶桂就立即逐條駁斥賽沖阿的參務章程修訂草案,以下僅就此例說明當時中央與地方官員對參 務管理的看法極為懸殊。
(1)賽沖阿首先要求有關燒鍋辦票一項改為核實交價,以省賣參交官的麻煩。賽沖阿認為燒鍋承領參票,多是出資交給攬頭代為買參交局,但後來演變為燒鍋領票一張,就出錢二百二十千文交攬頭代買,通常攬頭所承繳的人參質量都不佳。官方限於時限,無參枝可換,不得不將就驗收,這導致每年解進的官參的規格都不一致。他甚至明白點出解京的人參就只是作為預備賞給王公大臣之用,與其令燒鍋領票買參,還不如令他們直接繳交銀兩,這樣可以免去攬頭從中魚目混珠。他舉當時官參的售價為例,五等參一兩值銀一百四十兩,而燒鍋票一張應交五等參一兩二錢, 值銀一百六十八兩,兩者的差距不大,賽沖阿的作法似乎是出於現實考量。但中央官員可不這麼認為。大學士慶桂則轉述嘉慶皇帝的意見,認為燒鍋領票原意是要辦參,若是不要求燒鍋辦參,只令他們交出票價,這樣所交的銀兩則沒有正當的名目,於法無據。
(2)自乾隆朝開始,有關參余銀兩的問題以來就一直困擾著吉林的地方官。乾隆時經大學士奏准,客商購買余參時,必須按照成色,上參每收銀二十兩、中參收十六兩、下參收十二兩,以作為未能進山的臥票缺參及墊補刨夫塌欠之用。但這項措施容易造成各商唯利是圖,每當交參收參余時,多有以上報中、以中作下的弊病。賽沖阿因此建議,每參若買參一兩,無論上、中、下的成色,一律收銀十六兩。這些銀兩除非遇到刨夫塌欠,實在無可追究者,才動用來歸補缺額,其餘則盡收盡解。慶桂大學士則 再度搬出聖諭,駁斥說賽沖阿此作法無疑是影射向來參商有以多報少之嫌。
(3)賽沖阿建議每年的參余兩已是盡收盡解,該項目下有動用減票歸公的項目,請求裁除,以歸簡易。但慶桂認為這是遵循舊例,何況賽沖阿所提的第二項並未通過,所以並不可行。
(4)賽沖阿建議每年應進的四等參枝不應缺額,所有辦進的官參倘奉駁回,應由原交刨夫變價完繳。貴慶則認為刨夫多是無業貧民,若要求賠償,勢必無力償還,造成有名無實的狀況,反應該是由經手的將軍及參局人員或 照時價繳銀,或買參補額。
(5)賽沖阿認為向來吉林、寧古塔辦進大參應遵照以前的諭旨,無需辦進,以防秧參作偽。慶桂則搬出嘉慶七年的上諭,表示隨然不必另匣進呈大參,但偶而在山中尋獲大枝人參還是可以隨時進呈,不可隱匿;但沒有,也無需種植秧參造假。
欽差大臣文寧對賽沖阿的參務章程的意見和大學士慶桂的類似,他除了逐條駁斥賽沖阿的說法外,還對賽的另折奏片有不同看法。賽沖阿曾上奏稱說刨夫因官府查禁秧參,怕領票入山後所採挖的官參無法如數,大多觀望不前,並稱刨夫向來需要鋪戶接濟,後來因為積欠鋪戶,造成鋪戶不肯接濟刨夫,最後使得放票短少。但文寧卻認為:「秧參弊混全在攬頭」。他的觀察是:「現在秧參禁絕,領票何以更少,起其弊不在刨夫之裹足不前,在攬頭等之有心挾制,以為秧參禁絕,則官參斷不能足額,希冀仍准栽種秧參,其居心甚屬可惡,本年短放參票,皆由於此。」在文寧看來,問題不是出在秧參,而攬頭的從中宰控才是參票發放不足額的罪魁禍首。解決之道是吉林將軍應當要將禁絕秧參對刨夫是有益無害,向他們倡導,並找尋殷實的鋪戶作保,照例動用參 余銀接濟刨夫。如此一來,刨夫不至於拮据,攬頭亦不至於保持漁利。除了慶桂及文寧等中央官 員對秧參的看法與地方官員有完全不同的考量外,欽派侍郎英和的意見亦和賽沖阿的也有明顯的 不同。這些中央官員在嘉慶皇帝的施壓下,對於人參管理的辦法大多是站在刨夫立場上設想,這和身為地方官的吉林將軍賽沖阿似乎是站在身份地位較高的攬頭及燒鍋的立場考慮有所差異。
 結語 結語
透過嘉慶朝的秧參案,我們可以看出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東北經濟開發——更精確 地說是人參的採集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其中影響生態環境變遷的主要因素不是自然因素,而是官方的政策,尤其是國家權力對人參採集的介入。當我們把十九世紀初清政府對人參採集的政策放在更大的歐美學者的中國環境史研究或王利華先生所謂的社會生態史的脈絡來看時,80或許得到的答案會和以往學者的研究有所出入。荷蘭萊頓大學Eduard B. Vermeer在〈清代中國邊疆地區的人口與生態〉一文中曾提到:「有些學者相信,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饑荒與人口壓力的影響已大到使清廷無法再控制移民不去東北,並且以此作為中國人口過剩的證明。事實上,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大規模移民都被成功地防制。在1860年禁令部分取消時,中國人口已因太平天國之亂下降很多。而允許漢人移民邊區的動機是戰略上加強或『實邊』,而非騰空中國本部。在滿州,由於它的幅員以及困難的條件,農業聚落從南邊只是慢慢地擴張。公地首先開放,蒙古土地則比較晚。據估計在1914年只有四分之一的滿州荒地被開墾。大部分是平原旱地農耕。因此殖民對環境的衝擊仍相當有限。」81Vermee的結論認為,在清朝末年,政府支持東北移民,除了對吉林獵場的環境破壞的例子外,「移民實邊」對環境的衝擊仍相當有限。他的看法似乎忽略了 東北人參——尤其是秧參是觀察生態環境和國家權力互動的另一個有趣的例子。
對於清朝的中央官員而言,東北的盛京、吉林及寧古塔等地的參場人參產量的逐年減少,所要考慮的不是人參的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的問題,東北參場北移的現象日益嚴重,這可從嘉慶十七年(1812),清政府下詔令閒散旗丁前往吉林屯田的情況得知,《清史稿》提到:「八旗生齒日繁,亟宜廣籌生計。朕聞吉林土膏沃衍,地廣人稀,柳條邊外,參場遠移,其間空曠之地,不下千有餘裡,多屬腴壤,流民時有前往耕植。」這些官員所擔憂的反而是上繳官參足不足額,官參中摻雜的秧參數量多寡的問題,因此提出來改革方案大多是擴大參場或歇山的消極措施。當像吉林將軍秀林這樣的地方官員提出以秧參代替官參可增加參額數量時,就生態環境而言,或許未嘗不是一種可以減少人為的破壞,多給一些野生的山參繼續生長的機會,但當秀林提出種植秧參的建議的背後並非出自生態的考量,而是人參產量數字上的考量時,它所能帶來生態平衡的作用也就相當有限。尤其是當中央官員、甚至皇帝都認為:「盛京、吉林、寧古塔等處產毓人參,地靈鍾瑞,豈容已偽亂真」、「何必用人力栽養,近於作偽乎!朕向不服用參枝,但揆之物理,山內所產大參,其力自厚,若栽養之參,即服用亦不得力。」人參應該是野生的較佳,其餘不管是移植栽種,或者是以種子播種的,這些人參都是偽造的,其質量自然是「滋味薄弱」及「非真參可比」。 但對民間而言,秧參的使用已相當廣泛,深獲醫家及民眾的喜愛,例如《植物名實圖考》及載有:
「今紫團參以墾為田,所見舒城、施南山參尚不及黨參。滇姚州、麗江亦有參,形既各異,性亦多燥,為朝鮮附庸,陪都所產,雖屬人功,而氣味具體,人間服食至廣,即外裔如緬甸,亦由京都販焉。」陪都指的是盛京,該地所產的秧參深受民間肯定,不僅在北京販賣,甚至還外銷至緬甸。
本文的研究只是清帝國的人參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一環,嘉慶的秧參案不應只視為是清朝數百年的人參管理政策中的一個短暫變奏,它應該放在更大、更長時間的脈絡下來看,唯有如此,才能更深入瞭解秧參案的底層意義,以及清帝國對人參管理的特色。
|
|
 |
|
|
|